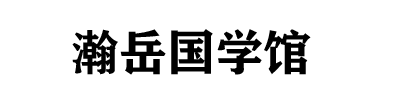昆曲历史:一、从昆山腔到水磨调
昆山腔形成于元末明初
根据明周元纬《泾林续记》的记载,说朱元璋曾问昆山老人周寿谊,“闻昆山腔甚佳,尔亦能讴否?”认为明初昆山腔已很盛行。据胡忌查证了明《蓬窗日录》、清《书影》、《锡金识小录》等书,周寿谊生于南宋景定年(1260-1264年),无锡人,长期居住在昆山,明洪武六年(1373年)朱元璋召见,当时周老人已有百余岁了。据此推算可以知道元朝末期已经开始流行昆山腔。
1960年,吴新雷看到了路工发现并珍藏的清初抄本《真迹日录》中的魏良辅《南词引正》,这是明末昆山人张丑根据文徵明手书真迹过录在《真迹日录》中的。这与明万历年《吴歈萃雅》中的《魏良辅曲律》有不同之处,其中有关于昆曲渊源的很重要的资料,特别是提到了元朝昆山顾坚善唱南曲,昆山腔形成于元末明初已不容置疑。第二年,钱南扬校注的《南词引正》在《戏剧报》正式发布,路工、傅惜华、周贻白等学者纷纷发表评论,把昆山腔发源的历史从明代向前推进到了元代。1989年,胡忌、刘致中的《昆剧发展史》也论证了这一观点。
《南词引正》中有关昆曲渊源的第五条是这样说的:“腔有数样,纷纭不类,各方风气所限,有昆山、海盐、余姚、杭州、弋阳。自徽州、江西、福建俱作弋阳腔;永乐间,云、贵二省皆作之,会唱者颇入耳。惟昆山为正声,乃唐玄宗时黄旛绰所传。元朝有顾坚者,虽离昆山三十里,居千墩,精于南辞,善作古赋。扩廓帖木儿闻其善歌,屡招不屈。与杨铁笛、顾阿瑛、倪元镇为友,自号风月散人。其著有《陶真野集》十卷、《风月散人乐府》八卷,行于世。善发南曲之奥,故国初有昆山腔之称。”
这里说昆山腔是唐玄宗时黄旛绰所传,只能看作是当地的传闻。唐代的宫廷乐臣黄旛绰名声很大,死后葬于昆山的绰墩,因昆山腔唱的南北曲中有源于唐代的教坊乐曲的成分,所以当地人就这样传说了。说到元代居住在昆山千墩的顾坚,“善发南曲之奥”,扩廓帖木)七听说他很能唱南曲,就多次命他来唱曲,但顾坚就是不去。顾坚其人,是研究昆山腔渊源的重要人物。据清《重修顾氏大宗世谱》、《南通顾氏家谱》,吴新雷根据顾坚同辈人的行年比照旁证,推知他成年后主要活动的年代,约在周德清写成《中原音韵》的元泰定元年(1324年)至元顺帝至正二十七年(1367年)之间,那么,自1324年至元亡的四十余年间,在昆山地区已经有昆山腔了。现知知名的第一歌手,就是顾坚。因此,根据魏良辅的《南词引正》,可以把昆山腔产生的年代大致推前到元泰定元年(1324年)。
据《明史·扩廓帖木儿传》,扩廓帖木儿是元末顺帝时的大臣,曾位居太尉、中书左垂相,后又封为河南王,代皇太子率军南下镇压农民起义,所以顾坚“屡招不屈”。而著名诗人杨铁笛(杨维桢),会稽人,居松江,善琵琶、笛、曲,常到昆山顾瑛家,在书画舫中“醉吹铁笛”。他写的南散曲如《夜行船序·苏台吊古》套很有名,也曾被人用昆山腔传唱,其联套格式[]夜行船序]、[前腔]、[斗蛤蟆]、[前腔]、[锦衣香]、[浆水令]、[尾声],也被昆腔沿用;名士顾阿瑛(顾瑛),昆山人,家甚富,筑有玉山草堂,草堂内有金粟轩、书画舫、春晖楼等多处建筑,好蓄养声伎,有女乐素云、素贞、小琼华、丁香秀、南枝秀等名伶,唱演南北曲;名画家倪元镇(倪瓒),无锡人,精音律,也喜欢写作北散曲,当时北曲的唱已对南曲的唱发生了一定的影响。这三人都是由元入明而卒于明初的,他们与昆山顾坚交游,都跟顾坚善唱昆山腔有关系。这些文士的艺文活动,赋曲雅会,和当时戏曲演唱的提高与雅化自有必然的联系。如杨维桢在《铁崖先生诗集》癸集中所记,在与官宦诗客宴会时,曾唤著名女伶沈青青来应唱《破镜重圆》戏文,予以重赏,并将“青青易名瑶水华”。诸如此类的文人雅事,对南曲的走向格律化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现知最早的南曲格律谱,是成书于元代天历年间(1328一1330年)的大元天历间《九宫十三调谱》(已佚,作者失考),明嘉靖年蒋孝的《南九宫谱》,就是承袭大元天历间《九宫十三调谱》修订编撰的。南曲的曲牌系统在元代天历年间已成雏形。
因此,在元泰定、天历年间,已经有用昆山腔来唱演南曲戏文和南曲散曲了。
早期昆山腔唱演南曲戏文和南曲散曲
从昆山腔的产生、流行到魏良辅等人对昆山腔的改造,其间约有二百年,但是早期昆山腔的发展非常缓慢,而且只在苏州地区主要在昆山一带流行。
元代后期,南戏流经昆山一带,唱南戏的海盐腔在苏州地区影响很大,南戏的唱与昆山当地的语言和音乐相结合,或说与昆山土腔相结合,在民间逐渐形成了唱南戏的一种新腔,这种新腔就被称为“昆山腔”。据现有资料考查,在这时期内,昆山腔所唱演的南戏并不很多,而流传下来的南戏和新创作的南戏却不少,据上面所引的《南词引正》的一段话就可知在南戏流布地区至少有昆山、海盐、余姚、杭州、弋阳等腔在唱演南戏。
约元至正二十二年(1362年),高则诚隐居于宁波南郊栎社沈氏楼(后称瑞光楼),完成了《琵琶记》的创作。高则诚常到昆山顾瑛家作客,顾瑛是唱曲行家,很可能《琵琶记》问世,就用当时的昆山腔唱了。元末明初人瞿佑(1341-1427年),作((一萼红·西厢待月》曲词中有“艳曲新腔,至今唱满吴娃”句,元王实甫的北曲《西厢记》也许已改作昆山腔唱了。
明嘉靖年间,徐渭撰写《南词叙录》,所谓“南词”即指南戏,它记录了嘉靖年以前的南戏剧目,称之为“宋元旧篇”的有六十六种,“本朝”的有四十八种,计有一百十四种。明万历年间又有吕天成写了本《曲品》,将嘉靖末年以前的南戏作品称为“旧传奇”,品评了“吴下俳优,尤喜掇串”的南戏剧目二十七种,它们是:《琵琶》、《拜月》、《荆钗》、《牧羊》、《香囊》、《孤儿》、《金印》、《连环》、《玉环》、《白兔》、《杀狗》、《教子》、《彩楼》、《四节》、《千金》、《还带》、《金丸》、《精忠》、《双忠》、《断发》、《宝剑》、《银瓶》、《娇红》、《三元》、《龙泉》、《投笔》、《五伦》。其中有些剧目虽然失传,但在当时曾“吴下盛演”;有些剧目的折子戏在流传过程中,经过曲家和艺人的不断加工提高,成为了昆曲的传统折子戏。现知,至少上述的二十七种南戏剧目,在苏州地区曾用昆山腔唱演;而不能排斥有些剧目在其他地区用其他的腔唱演,或曾用他腔唱演后来改由昆山腔唱演;也有二十七种以外的南戏剧目也曾用昆山腔唱演,如《绣襦》、《明珠》、《南西厢》等。
用昆山腔唱南曲散曲,如上文所说的杨铁崖的《夜行船序·苏台吊古》套,传有高则诚的《二郎神·秋闺》套,还有甚为流行的[念奴娇序〕套,等等。据比较可信的资料,明胡文焕编选的《群音类选》的“清腔类”中,就有相当数量的嘉靖中期以前的南散曲是用昆山腔传唱的。
这时期的昆山腔,我们称它为早期的昆山腔。它与弋阳腔、余姚腔、海益腔、杭州腔等并存,起初影响不大,在发展的进程中,不断吸收他腔的长处,改进自己的唱法;因为它的唱腔风格“流丽悠远”与“体局静好,以拍为之节”的海盐腔最为接近,所以吸收海盐腔的优点也最多。早期的昆山腔仍主要用弦索伴奏。还有一点也是很重要的,即个别唱曲家的精湛的唱曲水平,对早期昆山腔的提高也会起到一定的作用。如元末夏伯和的《青楼集》中记录的唱曲能手张四妈,审音知律,“南北令词,即席成赋”,“旧曲其音不传者,皆能寻腔依韵唱之”。夏伯和写《青楼集》时曾在昆山见到她,那时张四妈已年逾六十,“两鬓如黧,容色尚润,风流谈谑,不减少年时也”。我们不知她唱南曲用海盐腔还是昆山腔,但她晚年在昆山对唱南曲的昆山腔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又如上文说到的元末昆山人顾坚,“精于南辞”,“善发南曲之奥”,与好曲者交游,昆山顾瑛家常有的曲友雅集,必然会对唱曲艺术切磋研讨,改进和提高昆山腔的唱曲水平。
明代中叶昆山腔唱南曲在吴中渐成风气
昆山腔缓慢地发展了百余年,到了明代中叶,用昆山腔唱南曲在“吴中”已渐渐形成风气,流丽悠远的昆山腔已出乎三腔之上。我们仅从有限的资料也可以看出昆山腔在文人中间和民间的发展。
那时期,苏州地区经济繁荣、文化昌盛、人才辈出,书画诗文的成就蜚声江南。这些文人又大多喜欢声伎之乐,尤以正德年间(1506-1521年)江南才子唐寅、祝允明的艺事最为人乐道。唐寅,字伯虎,号六如,有诗云:“头插花枝手把杯,听罢歌童看舞女”,“龙虎榜中题姓氏,笙歌队里卖文章”。唐寅所作散曲几乎全是南散曲,以《步步娇·闺情》四套分咏春、夏、秋、冬最为著名,[步步娇]套的联套为:[步步娇]、[醉扶归]、[皂罗袍]、[好姐姐]、[香柳娘][尾]。这是昆山腔常用的套曲。后由魏良辅点板的《词林选胜》中就载录有唐寅许多南散曲。可惜《词林选胜》不传,但其所收之曲当是用昆山腔唱的。祝允明,字希哲,号枝山,聪慧绝伦,却不修行检,还常会傅粉妆扮,“从优伶间度新声”,“梨园子弟自谓弗及”。祝允明的南散曲《八声甘州·咏月》套传唱很广,这是一套用[解三醒]、[油葫芦]相互回环的“子母调”,这在当时还比较少见,联套为:[八声甘州]、[前腔]、[赚]、[解三醒]、[油葫芦]、[解三醒]、[油葫芦]、[解三醒]、[油葫芦]、[解三醒]、[油葫芦]、[解三醒]、[余文]。他还写有《新水令·春日闺情》南北合套。祝允明对当时的南戏声腔还很关注,他在著述《猥谈》中说“数十年来,所谓南戏盛行,更为无端,于是声音大乱”,_、正反映了当时昆山腔的流行及诸腔之间的相互影响。吕天成《曲品》说唐寅、祝允明是“不作传奇而作散曲者”,这里所谓的“传奇”是指当时的南曲戏文,不管是散曲还是南戏中的曲,若用昆山腔唱,实际是一回事。
与唐、祝差不多同时代的还有陈铎、徐霖、沈寿卿等人,陈铎、徐霖被称为“曲坛祭酒”,沈寿卿也“名满大江南北”。陈铎,字大声,号秋碧,生平豪爽,妙解音律,“时操筝琶寻声度曲,即教坊子弟听之,自恨其技弗如也”,称其为“乐王”。其所作散曲,“文采风流,冠绝一世”,以北散曲著名,也偶作南散曲。魏良辅把他的《秋碧乐府》与《琵琶记》同作为练唱昆腔的范本。徐霖,字子仁,号髯仙,“每当筵自度曲为新声”,“江左言风流者必首髯仙”。
正德皇帝南巡时,曾被推荐为武宗作曲,备受宠幸,武宗曾两次幸其南京家邸,欲授教坊司官,固辞不受,乃授锦衣卫镇抚。曾于南京武定桥东筑快园,命伶童侍女演戏自娱,与江南名士交游,既作南散曲也作南曲戏文,曾作南戏八种,其中《三元记》(或谓沈寿卿作)、《绣褥记》为其传存之作。沈寿卿,以字行,精乐律,“撰歌曲,教童奴为俳优”。正德皇帝南巡时亦曾召见,沈一夕而作《四喜》戏文,武宗喜甚,欲授官,沈不受而归。其尚作有《三元记》、《龙泉记》、《娇红记》(后有孟称舜同名传本)。据吕天成《曲品》,沈寿卿所作南曲戏文,“语或嫌于凑插,事每近于拘迂”,评价不高,然其剧多为昆曲场上之作,“吴优多肯演行”。
到了嘉靖年间,用昆山腔唱演的南曲戏文,出现了颇有影响的作品,如《明珠记》和《南西厢》。
陆采的《明珠记》是根据唐人小说《刘无双传》编剧的,写刘无双与王仙客的奇异的恋情故事。据《列朝诗集小传》云:“曲即成,集吴阊教师精音律者,逐腔改定,然后妙选梨园,登场教演,期尽善而后出。”所谓“逐腔改定”,当然是以昆山腔的唱法来改定南曲曲词。这戏在当时及后来常被演出。说到《南西厢》,就更为人们注目。因元王实甫的北曲《西厢记》影响很大,将此剧改为南曲用昆山腔唱演,也是必然的事。流行的李日华《南西厢》,实际是由海盐人崔时佩编集,经李日华新增校定的,将北曲《西厢记》改作用昆山腔唱演的南曲,尽管有损元本文字,时人“冷齿”,但李日华本还保留有王实甫文字,还是在戏场流行开来了。陆采不满于李日华本翻北为南,有失原本的措辞命意,便自诩“天与丹青手,画出人间万种情”,走了另一极端:“悉以己意自创,不袭北剧一语”,为昆山腔新编《西厢》南曲本。结果,新编本不受欢迎,戏场流行的依旧是李日华本而不是陆采本。这是一件耐人寻味的事。自此以后,为昆山腔编写南曲戏文的作家也就渐渐多了起来。
魏良辅等人对昆山腔的改造
昆曲史上最为重大的事,那就是魏良辅等人对昆山腔的改造。在昆曲界,学者一般说魏良辅是明嘉靖、隆庆间人,那是指他的活动时期。胡忌、刘致中的《昆剧发展史》以同时期人的生卒推算他约生于明弘治十四年(1501年)前后,卒于万历十二年(1584年)前后。在他的生年中,跟昆曲关系最为重大的是: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或谓二十二年(1543年)已写成《南词引正》;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前后,“时称昆山腔者皆祖魏良辅”。这就是说,在嘉靖中晚期,魏良辅不仅完成了对昆山腔的改造,创造了“水磨调”的唱法,而且使水磨调的唱法成为昆山腔的正宗。
《南词引正》和《词林选胜》是魏良辅改革昆山腔的重要著作,可惜《词林选胜》至今没有被发现。
关于魏良辅的生平记载很少,明万历昆山人张大复《梅花草堂笔谈》说:“魏良辅别号尚泉,居太仓之南关,能谐声律,转音若丝。”明末清初隐居苏州的余怀《寄畅园闻歌记》说:“良辅初习北音,绌于北人王友山,退而镂心南曲,足迹不下楼十年。当是时,南曲率平直无意致,良辅转喉押调,度为新声。”居于太仓南关的魏良辅,是著名的唱曲家,由唱北曲然后潜心钻研南曲。据一些笔记资料,我们知道魏良辅改革昆山腔还未成功之前,与昆山陶九官和苏州周梦谷、滕全拙、朱南川齐名,周梦谷唱“官板曲”的名气似乎更响。还有他的前辈曲家如北人王友山,户侯过云适,昊中老曲师袁髯、尤驼等,在苏州地区皆享有盛名。
魏良辅研习昆山腔,吸取了北曲中州调和海盐腔的唱法,每有心得,必去请教驻军太仓南关的户侯过云适,待善曲的过云适满意乃止。同里曲家陆九畴,曾与魏良辅竞唱,比试之后即愿出其门下。当时,师事魏良辅,一起研习唱法的有太仓或昆山的张小泉、季敬坡、戴梅川、包郎郎、周梦山等,还有无锡的潘荆南、陈梦萱、潘少泾等,而最为人所乐道的是魏良辅之婿张野塘。明沈德符《顾曲杂言》说:“吴中以北曲擅场者,仅见张野塘一人。”据明末宋直方《琐闻录》,张野塘,河北人,因犯罪被发配来苏州太仓。魏良辅闻其善歌,曾留听三日夜,赞赏不绝,就与其结交。当时魏良辅五十余岁,有一女,也善唱曲,于是招张野塘为婿。自后,张野塘习南曲,更定弦索音节,使与南音相近,并改良三弦,名弦子。后来,张野塘之子以提琴闻名,传给杨六,杨六又有改进,使与弦子相配,乐声更为柔曼婉畅,时人称之为“江南名乐”。张野塘实际成了魏良辅改革昆山腔的重要助手。
魏良辅对昆山腔的改造,伴奏乐器的改良也是相当重要的。据《寄畅园闻歌记》,跟随魏良辅一起改革昆山腔的,还有苏州张梅谷,善吹洞箫,以箫从曲;昆山谢林泉,善擫管,以管从曲。而在无锡的陈梦萱、顾渭宾、吕起渭也以箫管擅名。在无锡有魏良辅的学生潘荆南唱曲也必借箫管合,一时在曲界竞相传习。后来,明潘之恒在《弯啸小品》卷二《叙曲》中曾说起当时昆腔乐师:“秦之箫,许之管,冯之笙,张之三弦,其子以提琴鸣,传于杨氏。如杨之摘阮,陆之搊筝,刘之琵琶,皆能和曲之微,而令悠长婉转以率顿挫也。”明徐渭《南词叙录》也曾说“今昆山以笛、管、笙、琵按节而唱南曲”。在魏良辅改革昆山腔时,伴奏乐器已得到很大程度的发展,在笛、管、笙、琵琶、鼓板外,又增加了箫、三弦、提琴、阮、筝,彻底改变了弦索配南曲的“方底圆盖”的现象。这样一个比较齐全的管弦乐器的组合,无疑更能使昆山新腔发挥“悠长婉转”、“转音若丝”的特点。
魏良辅改革昆山腔曾得到许多人的帮助,在他的周围自然形成了一个改革群体。他的最大功绩是对昆腔唱法的改进与提高,在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写成的《南词引正》,就是他毕生唱曲经验的总结。根据《南词引正》和明末沈宠绥《度曲须知》,就能知道魏良辅新腔唱曲的艺术特点和他所取得的成就。他绝不满意原昆山腔的“讹陋”和“平直无意致”,于是力求洗尽乖声,转喉押调,度为新声。他认为曲有三绝:字清为一绝,腔纯为二绝,板正为三绝。唱曲五音以四声为主,平上去入既要端正又要“婉协”,字音的头腹尾要唱得“毕匀”,启口轻圆,收音纯细。唱长腔“贵圆活”,唱短腔“要遒劲”;过腔接字乃“关琐之地,最要得体”,要交代清楚。拍板“最要得中”,须要板眼分明。对于双叠字、单叠字、唇齿音字、闭口音字,南不杂北,北不杂南,都非常讲究。经改革的昆山新腔更是柔美婉转、清俊温润,时人谓之“水磨调”。魏良辅度曲以清唱时曲,又谓之“冷板曲”。
魏良辅自得张野塘后,也改良了北曲昆唱,“南曲不可杂北腔,北曲不可杂南字”,以使“字清腔劲”。明张大复赞其唱“转音若丝’,,余怀论其唱“跌换巧掇,恒以深邈,助其凄唳”,明沈宠绥评其唱“功深镕琢,气无烟火”。吴中老曲师如袁髯、尤驼者,皆自以为不及魏良辅。在当时,昆腔的唱法形成昆山、苏州、无锡三派,各具风格。苏州一派时称“吴腔”,即早期与魏良辅齐名的邓全拙,“稍折中于魏”,影响也很大。无锡一派“媚而繁”,“宗魏而艳新声”,实际乃是魏的传人潘荆南、陈梦置、潘少泾辈。人说“三支共派,不相雌雄,而郡人能融通为一”,实际都有魏良辅改革的影响,明潘之恒评曰:“锡头昆尾吴为腹,缓急抑扬断复续”。约在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前后,魏良辅已“立昆之宗”,“时称昆山腔者,皆祖魏良辅”。然而,魏良辅改革昆山腔,“调用水磨,拍捱冷板”,“腔曰昆腔,曲名时曲”,虽“声场禀为曲圣,后世依为鼻祖”,然是唱清曲的“清工”,时人也称之为“吴歈”。至于将“水磨调”搬用到戏台上去唱,成为“戏工”,那是晚一步的事了。在明代将魏良辅改革后的昆山腔,遂称之为“昆腔”,或“昆腔新声”,或“水磨调”。
梁辰鱼得魏良辅唱曲之传后作传奇《浣纱记》
魏良辅改革昆山腔并规范了“水磨调”的唱法,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这个新腔要继续得到完善和发展,还需要有更多的唱曲家的实践和研究,在更大的范围内扩展影响。这就需要几代传人的努力和走向戏台。
据明张大复《梅花草堂笔谈》,魏良辅改革昆山腔,昆山“梁伯龙闻,起而效之”,他考订元剧,自翻新调,与郑思笠、唐小虞、陈梅泉等五七人,精研音理。当时,唱曲与听曲者“取声必宗伯龙氏,谓之昆腔”,可谓“梁派”。嘉靖末隆庆初,昆山又有一派张新的“张派”,对昆腔新声仍不满足,“乃取良辅校本,出青于蓝”,他与赵瞻云、雷敷民和其叔张小泉(魏良辅的学生),踏月邮亭,往来唱和,号称为“南码头曲”。跟随他学曲的有顾氏兄弟仁茂、靖甫,仁茂授陈元瑜,靖甫授谢含之,“为一时登坛之彦”。张派实际是“禀律于梁,而以其意稍为均节”,标新立异而已。其时梁派的声誉很大,郑思笠的学生李季膺,就被人称为“嫡派”。无论梁派、张派,都可以看作是魏良辅的传人。犹有无锡安撝吉、常熟周似虞也曾受教于魏良辅。安撝吉自云受之于魏,唱昆腔“有宫有调”;周似虞向魏良辅学曲,“曲尽其妙”,每当中秋坐虎丘生公石上,开喉一唱,千人石上“寂寂无一人”。此二人的唱曲活动直延续到明末。据明末徐于室、钮少雅《九宫正始·自序》,明末著名曲师钮少雅曾向魏的传人张新、吴芍溪、任小泉、张怀仙学曲,穷研探微,精订曲谱,“虽不能入魏君之室,而亦循循乎登魏君之堂”。有清一代的唱曲,视为正宗者皆祖钮少雅。凡此,均可见魏良辅改革昆山腔的成果香烟不绝,绵延数百年,这是余话了。
在明嘉靖、隆庆年间,梁辰鱼对昆腔的贡献是仅次于魏良辅的。梁辰鱼(1519-1591年),字伯龙,昆山人,疏眉虬髯,任侠好游,以诗、行草闻名,尤其喜爱度曲,“得魏良辅之传,转喉发调,声出金石”。梁辰鱼聚集曲友研习魏良辅昆腔的唱法,并作有《江东白芋》散曲集,不仅在上层社会富贵之家传唱,也在民间传唱,所谓“丽调喧传于《白芋》,新歌纷咏于青楼”。据清焦循《剧说》所引《蜗亭杂订》说:“梁伯龙风流自赏,修髯,身长八尺,为一时词家所宗。艳歌清引,传播戚里间……歌儿舞女,不见伯龙,自以为不祥也。其教人度曲,设大案,西向坐,序列左右,递传迭和。”他在传播昆腔新声中起了很大的作用。嘉靖、隆庆年间,他又发挥自己文学的特长,按昆腔新声将早年的《吴越春秋》改作为昆腔传奇《浣纱记》,使昆腔新声走上戏台。这是昆曲发展史上很重要的转折点。
梁辰鱼的《浣纱记》以春秋时代昊越相争的故事为题材,肯定了越国君臣的复国精神,在这慷慨悲凉的情节发展中,以西施和范蠡的悲欢离合为情节发展的主线,适应了观众的欣赏习惯。该剧以人们熟知的政治斗争为背景,拓展了戏剧场面,在此基础上突破了南戏以来的生旦格局,以充满诗情画意的“泛湖”结尾,剧中诸人物的形象特征鲜明,令人耳目一新。曲词虽没有摆脱当时风行的骄俪派的风格,文采翩然,但也有清新生动之句。《浣纱记》初出,便在青浦县令屠隆家中由优人演出。该剧平仄甚谐,宫调不失,排场热闹,场面富丽,以昆山新腔唱新词,一时盛传剧坛,流传后世。明王元美诗云“吴阊白面冶游儿,争唱梁郎雪艳词”,清初吴伟业也有诗云“里人度曲魏良辅,高士填词梁伯龙”。直到清代末期,该剧几乎能全本演出,而在戏场流传至今的折子戏尚有《回营》、《打围》、《寄子》、《拜施》、《分纱》、《进美》、《采莲》诸折。
差不多与《浣纱记》同时出现的还有无名氏的《鸣凤记》,传说为王世贞作,也有人说是唐凤仪所作。《鸣凤记》也是值得重视的传奇,它以嘉靖年间现实的政治斗争为题材,表现了复杂、激烈而动人心魄的政治斗争。剧中以严篙、严世蕃、赵文华等为权奸一方,以夏言、杨继盛等“八谏臣”为忠义一方,穿插了众多人事的情节,善恶对照,忠奸都有鲜明饱满的形象。剧中尤其突出地赞颂了杨继盛忧国忧民、嫉恶如仇、刚强忠烈的品质。该剧的结构非常特殊,线索复杂而繁多,但能一环扣一环,以邹应龙、林润定交始,以邹、林败篙终,中间穿插人物和史事,并使之能得到正确的表现。因为它反映的是人们关注的现实斗争,所以很快在戏场流行起来。据清焦循《剧说》所载,曾被严世蕃玩弄的海盐腔优伶金凤,在严篙父子败后沦落为贫民,在《鸣凤记》中扮演严世蕃,演来酷肖其人。其时昆腔盛行,唱海盐腔的金凤改唱昆腔,也在情理之中。该剧流传下来,其中《河套》、《写本》是最精彩的折子戏。
在明代的嘉靖末、隆庆、万历初这一特定的时期,将昆腔新声搬上舞台演戏,很难说《浣纱记》是第一部,但可以说《浣纱记》是最成功的一部。据万历初刊刻的((八能奏锦》,这一时期尚有《红拂记》、《玉块记》、《狮吼记》、《玉簪记》等用昆腔唱,也或用昆腔新声唱,但有的戏可改调歌之,惟《浣纱记》不能改调唱。自此,清柔而婉转的昆腔新声随着舞台演出传播江南江北,新创作的昆腔传奇也不断涌现,开创了昆腔传奇的新时代,从而奠定了昆曲在中国戏曲发展史上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