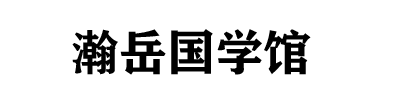昆曲历史:八、风雨经年枯枝春发
建国后昆曲的复苏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南北昆曲演员受到重视,并开始活跃起来,主要的昆曲演员得到了政府的安排,昆曲演员归位。1949年10月,在开国大典的庆贺晚会上,北昆侯永奎应邀在怀仁堂演出《林冲夜奔》。接着,北昆名角韩世昌、白云生、侯永奎等受聘为华北人民文工团教员,并在北京长安大戏院演出昆曲。政府还将在河北农村的侯玉山、孟祥生、魏庆林、侯炳武、白玉珍等接到北京。不久,在华北人民文工团的基础上成立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不少北昆演员就在剧院任教员,后侯玉山调任解放军总政文二巨团舞蹈教师。
在南方,1949年11月,朱传茗、沈传芷、张传芳、郑传鉴、汪传铃、方传芸、王传蕖、沈传芹、薛传钢、周传沧、周传瑛、沈传锟等“传字辈”演员在上海会合,以原“新乐府”的名义在同孚大戏院连续演出一个月。梅兰芳、俞振飞也在中国大戏院演出《游园惊梦》,“传字辈”演员参演《堆花》。年后,“传字辈”演员移师恩派亚大戏院继续上演昆曲。俞振飞参演《梳妆·掷戟》,后随梅兰芳剧团赴天津演出《断桥》。1951年4月,“传字辈”演员应邀赴苏州开明大戏院演出昆曲,苏、沪曲友也参与了演出。在此期间,汪传铃被安排入新安旅行团(上海歌剧院前身)任教,方传芸入上海戏剧专科学校(上海戏剧学院前身)任讲师,1951年3月华东戏曲研究院成立后陆续聘请了朱传茗、沈传芷、薛传钢、郑传鉴、张传芳、周传沧、华传浩、王传蕖等任职。建国初期,只有浙江的三个昆曲团:周传瑛、王传淞所在的国风苏剧团易名为国风苏昆剧团,后在杭州改名为“国风昆苏剧团”;温州的原新同福、新品玉等流散演员成立了巨轮昆剧团,后改名为“永嘉昆剧团”;金华地区宣平县由民生乐社坐唱班改建的宣平昆剧团,后改名为“武义昆剧团”。
在“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方针的指导下,昆曲演员从绝境中走出,以强烈的翻身感和事业心继续着古老昆曲的传世事业,投身于建国初期的“戏改”工作,对于昆曲艺术也有了新的认识。昆曲的复苏,从一开始就在新的思想指导下,注重于剧目的精益求精和改革出新,并在演出实践中,使古老的昆曲艺术焕发出新的生命。
为纪念世界文化名人洪异逝世二百五十周年,由张宗祥发起,田汉、洪深促成,浙江国风昆苏剧团于1954年夏起尝试改编洪昇名作《长生殿》。改编强调了原著的思想性,采用原著的《定情赐盒》、《进果》、《鹊桥密誓》、《小宴惊变》、《骂贼》、《埋玉》诸出,重新进行整理编排。其中《骂贼》、《埋玉》两出的表演久已失传,系全新设计表演,仍与流传的《长生殿》折子戏的表演十分和谐。后来,该剧又进行修改,《进果》一出后增《舞盘》、《傍讶》,《密誓》后增《边报》,删去《骂贼》一出,把戏集中在李、杨爱情悲剧的主线上,使全剧情节流畅,主题鲜明,传统的表演艺术得到了更好的发挥。该剧由周传瑛饰唐明皇,张娴饰杨玉环,王传淞饰高力士,沈传锟饰杨国忠,周传铮饰安禄山,包传铎饰陈玄礼,朱国梁、张艳云饰算命夫妇,在杭州、上海、北京先后公演,社会效果极佳。他们又对《风筝误》及折子戏《下山》、《出猎·回猎》、《梳妆·跪池》等也进行了加工提高,去芜存著。这些点点滴滴的改革举措,已在“推陈出新”的道路上走出了最初的一步。
1954年春,华东戏曲研究院招收的建国后第一批昆曲学员开学,主要由“传字辈”演员任教,第二年上海市戏曲学校正式成立,该班即为第一届昆曲演员班,继续学戏。数年后,该班学员成为中国昆曲舞台的骨干演员。1954年9月至10月,在上海举行了第一届华东戏曲观摩演出大会,浙江国风昆苏剧团赴沪,上海、杭州两地的“传字辈”演员合作演出,王传淞的《相梁·刺梁》、朱传茗的《思凡》、周传瑛的《长生殿·小宴》、华传浩的《醉皂》等皆精妙绝伦,尤其是汪传铃和方传芸借鉴乱弹新创排的昆曲小武戏《挡马》,技艺超群,众口交赞。这次演出,既体现了“双百”方针的正确,也显示了古老昆曲的无比魅力。1955年2月,北京举行昆曲演出,上海的朱传茗、沈传芷、华传浩、汪传铃、方传芸等演出《断桥》、《醉皂》、《挡马》、《芦林》,月匕京的韩世昌、白云生、侯玉山、侯永奎、白玉珍、马祥麟、魏庆林、傅雪漪等演出《饭店认子》、《胖姑学舌》、《琴挑》、《夜巡》、《钟馗嫁妹》,历经风雨的南北昆曲演员在北京欢聚一堂,为建国后南北昆曲的观摩交流开了先声。
满城争说《十五贯》
建国后昆曲改革的第一大成果,当属浙江昆苏剧团的《十五贯》。1956年4月,该剧在北京演出四十六场,出现了满城争说《十五贯》的盛况。
《十五贯》自清初创作以来,演出近三百年,“传字辈”演员保留了十余出戏,还经常串演“全本”,国风苏剧团时期也曾演出过昆曲苏滩合唱本,在观众中有一定的影响。为了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有所创新,1955年,浙江省文化部门领导黄源、郑伯永和国风昆苏剧团的周传瑛、王传淞、朱国梁、陈静组成六人小组,着手整编该剧,集体讨论,陈静执笔,边改边排,边排边改。1956年1月完成排演,全剧八场:《鼠祸》、《受嫌》、《被冤》、《判斩》、《见都》、《踏勘》、《访鼠》、《审鼠》。新年伊始,便在杭州、上海试演,受到文艺界的好评,陆定一邀请《十五贯》剧组进京汇报演出。4月1日,浙江省文化局宣布国风昆苏剧团改制为国营浙江昆苏剧团,周传瑛为团长,蒋笑笑为副团长,并于4月5日率团进京演出。先是两场观摩演出《十五贯》、《长生殿》;自4月10日至5月27日在广和剧场公演《十五贯》,观众达七万余人,引来满城争说《十五贯》的盛况;其间,还到中南海怀仁堂演出《十五贯》,受到中央领导的接见,周恩来总理回京即去广和剧场看戏,给予了支持和鼓励。5月18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从“一出戏救活了一个剧种”谈起》。从当时的昆曲境遇而言,《十五贯》虽非尽善尽美,但它确实改变了昆曲的处境,对昆曲的生存和发展起到了很大的历史作用。
《十五贯》载誉而归时,沿途在天津、济南、南京、镇江、苏州等地演出,也频获赞誉。7月即由上海电影制片厂拍成舞台艺术片,传播全国及东南亚。这时,全国各地剧种普遍移植《十五贯》,争相上演,时称“千千万万贯的《十五贯》”,影响极大。在1957年紫光阁会议上,周总理说:“昆曲受过长期的压抑,但是经过艺人们的努力奋斗,使得这株兰花更加芬芳了。”自此以后,昆曲殊获“兰花”的雅称。
《十五贯》是昆曲“推陈出新”的范例,剧本改编成功,演员表演精彩。改编本批判地方官过于执的主观臆测和过于自信,批评周忱的官僚处世哲学,颂扬清官况钟的实事求是和调查研究,以及为民申冤不惜前程的精神。这三个典型,均具有很强的现实教育意义。改编本删除一条线索,以熊友兰与苏戌娟的冤情为情节线索集中提炼,突出思想教育意义,塑造典型人物形象,保留传统精华,情节紧凑,语言通俗。改编本既有主题倾向的时代性,又有戏剧内涵的哲理性。舞台表演上将重点放在况钟、娄阿鼠、过于执、周忱四角身上,分别由周传瑛、王传淞、朱国梁、包传铎扮演,各擅其长。尤其是周传瑛与王传淞的表演,有口皆碑。周传瑛以小生行演老生,打破程式化的表演,融合老生的稳重严肃与小生的风雅潇洒,动作目的性强,简练而不重复;与朱国梁、包传铎、王传淞的对手戏《踏勘》、《见都》、《访鼠》,分寸适度,紧扣人心,处处见性格;在《访鼠》中勾心斗角而又妙趣横生,精妙之极。王传淞底子深厚,所演丑角娄阿鼠以技巧擅胜,注重人物的外形与内心刻画入微,无处不活灵活现;《鼠祸》的出场,《受嫌》的混迹人群,其举手投足,挤眉弄眼,缩颈哈腰转身,既有鼠形又有贼性;尤在《访鼠》一场,调动浑身解数,以五官挪位的表情技巧、凳上矮子功的变化无穷,加上白口的语气声调,跟周传瑛的“测”配合得恰到好处,纹丝不差,二者对立统一,水乳交融,处处表现出人物的内心矛盾,可谓“绝活”。
《十五贯》是建国初期昆曲改革的杰作,也是昆曲走上再兴之路的标志。
《十五贯》对昆曲界的巨大影响
《十五贯》的成功,推动了昆曲的发展步伐,对昆曲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的关怀下,昆曲得到了格外的重视,整编剧团,组织演出,昆曲接班人走上舞台,四、五年间形成了中国昆曲的基本格局。
当时,昆曲剧团只有上文所说的浙江三家,浙江昆苏剧团、永嘉昆剧团和宣平昆剧团(1957年改名武义昆剧团)。《十五贯》演出成功后,1956年10月,江苏在苏州市苏剧团的基础上成立了江苏省苏昆剧团。1957年6月,北京在北方昆曲代表团的基础上成立了北方昆曲剧院。1957年11月,湖南嘉禾创办湘昆学员训练班,由原“昆文秀班”艺人任教,在此基础上于1960年2月成立郴州专区湘昆剧团,1964年9月改名湖南省湘昆剧团,1966年3月改名湖南省昆剧团。1960年3月,在北方昆曲剧院的影响下,河北文化部门召集流散的北昆教师和演员,在保定市京剧团的基础上成立河北省昆曲剧团,同年6月即与河北省京剧团合并,改名河北省京昆剧团。1961年8月,由原上海戏曲学校昆班、京班的学员组成上海戏曲学校京昆实验剧团,1962年8月改名上海青年京昆剧团。昆曲的艺术队伍经整编后,全国各地已有八个演出团体。
《十五贯》的成功,直接推动了昆曲的演出活动。1956年9月,在苏州举办了昆曲观摩演出,“传字辈”演员周传瑛、王传淞、朱传茗、华传浩、郑传鉴、张传芳、包传铎等,还有京、沪、苏、浙的白云生、马祥麟、俞振飞、徐凌云、徐子权、张娴和青年演员张继青等,另有上海戏校的学员和沪、苏的曲友也参加了演出。接着,11月在上海举行了第一次南北昆曲大会演。北京组织了以韩世昌为首的北方昆曲代表团赴沪,主要演员有韩世昌、白云生、侯永奎、马祥麟、侯玉山、傅雪漪、沈盘生、徐惠如等,还有青年演员李淑君、丛兆桓、孔昭、崔洁、林萍等;浙江有以周传瑛、王传淞为首的浙江昆苏剧团的主要演员和“世字辈”随团学员;上海有俞振飞、言慧珠、徐凌云、朱传茗、张传芳、沈传芷、华传浩、郑传鉴、汪传铃、方传芸、王传蕖、薛传钢、周传沧、顾森柏、郭建英等,以及上海戏曲学校昆班学员。共演出二十六天三十场,一百二十四个折子戏和五个本戏《白罗衫》、《渔家乐》、《十五贯》、《长生殿》、《贩马记》。这次南北昆曲的示范交流,显示了昆曲丰厚的艺术传统,昆曲学员的演出亦颇引人注目。会演后,北方昆曲代表团应邀赴杭州、苏州、南京继续交流演出。南北昆曲的交流演出社会影响很大,可以说是近百年昆曲演出史上绝无仅有的盛举。
此外,各地昆曲剧团组建后都有频繁的演出活动,就是在河北文安、雄县、霸县、静海的昆弋子弟会和浙江建德、兰溪的坐唱班组建的小昆团也在当地乡镇多次演出,业余的曲社曲友也兴致勃勃举行同期唱曲或串演活动。
值得一说的是,这一时期,各地纷纷开班培养昆曲接班人,经过几年的努力,昆曲学员逐渐从课堂走上了舞台,给古老的昆曲舞台吹进了一股春风。
较早培养学员的要算是国风昆苏剧团,1952年,该团随团子弟就开始以“世字辈”排名;改制为浙江昆苏剧团后,1960年开始培养“盛字辈”(后未以“盛”字排辈)学员。1956年成立的江苏省苏昆剧团,当时已有1953年苏州市民锋苏剧团培养的“继字辈”,改建为江苏省苏昆剧团后,又接着培养“继字辈”学员,1959、1960年间开始培养“承字辈”(后未以“承”字排辈)学员。1955年上海戏曲学校的昆班是1954年华东戏曲研究院招收的,1959年又招收一个昆班,前后两班时称“昆大班”与“昆小班”。而后各地相继招收昆曲学员,有1957年湖南郴州专区开办的嘉禾昆曲学员训练班,三年后在该班基础上成立郴州专区湘昆剧团;1957年温州专区戏曲学员训练班昆曲班为永嘉昆曲团招收学员;1958年北方昆曲剧院成立学员班;1958年江苏省戏曲学校创办昆曲班;1959年浙江省戏曲学校也创办昆曲班;1959年河北的高阳县北昆戏曲学校开办招生,两年后该校并入河北省戏曲学校昆曲科;1960年苏州专区戏曲学校设立苏昆班;1961年浙江的武义昆剧团为金华昆曲开办昆曲演员培训班。
最早走上昆曲舞台的学员也是浙江国风昆苏剧团的“世字辈”,接着是江苏省苏昆剧团的“继字辈”和北方昆曲剧院的青年演员,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相继登上舞台。60年代初,上海戏曲学校“昆大班”也走上舞台,后组建京昆实验剧团,又改建为上海青年京昆剧团。这时期,在南北昆曲舞台上最亮丽、最有青春朝气的昆曲演出,就是由各地培养成才的年轻的昆曲演员表演的。
1956年挂牌的浙江昆苏剧团,已有历年来培养的“世字辈”早期青年演员,如朱世藕、龚世葵、王世瑶、张世萼、汪世瑜、张世铮、沈世华、王世菊等,在随团演出中,得到“传字辈”的提携,成绩斐然。早在1953年,张世萼、朱世藕就在《牡丹亭》中分饰柳梦梅、春香。1958年在南京演出《风筝误》、《鸣凤记》期间,“世字辈”就在南京大学和世界剧场演出折子戏,有张世萼、包世蓉、徐冠春的《断桥》,汪世瑜、顾世芬的《琴挑》,张世琤、杨世汶、吴世芳的《连环记·小宴》,华世鸿、周世瑞的《问探》,钦世江、王世菊、顾世芬的《闹学》等。“世字辈”学戏早,能戏多,在当时是很主要的一批青年演员。
1957年春节期间,江苏省苏昆剧团“继字辈”演员组队在江苏、上海的市县乡镇作实习巡演,扩大青年演员的影响。1957年江苏省首届戏曲观摩大会,“继字辈”参演了《断桥》、《访鼠测字》,张继青、柳继雁初露头角。1960年,以张继青、范继信、姚继焜等十三名“继字辈”演员赴南京,与江苏省戏曲学校首届昆班学员合并,组建驻地南京的江苏省苏昆剧团,与苏州原团异地并存,加强青年团的力量。1961年,两团联合在上海公演,历时十九天演出二十四场,剧目有《盗令》、《杀惜》、《思凡》、《断桥》等,张继青主演的《痴梦》、《窦娥冤》蜚声剧坛,回南京后继续在世界剧场公演,沪、宁两地的专家对江苏培养的成批的青年演员备加赞扬。
1957年北方昆曲剧院建院时,已有青年演员侯少奎、白士林、李淑君、丛兆桓等,后来又有本院培养的洪雪飞、张玉文、许凤山、马玉森、张敦义等青年演员,新人的队伍也比较强,。在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北昆舞台散发出沁人的清香。北昆编演的几台大戏《文成公主》、《李慧娘》、《晴雯》、《渔家乐》,青年演员大多担任了主要角色,频获观众赞赏。李淑君、侯少奎的《千里送京娘》,李淑君的《奇双会》、《昭君出塞》,侯少奎的《单刀会》、《夜奔》,张玉文的《棋盘会》,白士林的《挑滑车》,周万江的《山门》,洪雪飞的《活捉》、《斩娥》等,各擅其能,表现了鲜明的北昆特色。
1957年,上海戏曲学校昆班学员,在长江剧场首次实习公演《出猎回猎》、《游园惊梦》、《钟馗嫁妹》、《问探》、《寄子》等后,就经常在舞台上展现风采,而后又排演了《连环记》、《渔家乐》、《拜月亭》、《调风月》、《牡丹亭》等大戏。在1961年毕业之前,华文漪、张洵澎、岳美缇、王芝泉、梁谷音、刘异龙、蔡正仁、王英姿、金采琴、计镇华、顾兆琳、方洋、张铭荣等已小荷初露,深得观众喜爱,演出的折子戏如《游园惊梦》、《琴挑》、《偷诗》、《断桥》、《盗草》、《长生殿·小宴》、《迎像哭像》、《弹词》、《拾柴·泼粥》、《出猎回猎》、《走雨·踏伞》、《问探》、《拜月》、《湖楼·受吐》、《相梁·刺梁》、《寄子》、《思凡》、《下山》、《醉皂》、《盗甲》、《三闯》、《山门》、《挡马》、《扈家庄》、《百花赠剑》、《钟馗嫁妹》等,色彩纷呈。1960年的进京演出和在济南、蚌埠、芜湖等地的巡演,华文漪等青年演员已受到戏曲界的注目。1961年毕业前后排演《红楼梦》、《白蛇传》、《墙头马上》,12月以“上海青年京昆剧团”的名义赴香港演出,被香港新闻界誉为本港的一件盛事,回沪时又在广州演出,上海“昆大班”以整齐的阵容、精彩的演出赢得了广泛的好评。
1962年12月,苏、浙、沪两省一市的昆曲会演在苏州举行,参演的剧团有江苏省苏昆剧团、浙江昆苏剧团、上海青年京昆剧团、上海戏曲学校昆班、永嘉昆剧团、武义昆剧团等六个昆剧团五百余人,演出十四场。参加演出的青年演员、学员达四百人,占出场演员的百分之八十,标志着昆曲后继有人的欣欣向荣局面。张继青、汪世瑜、华文漪等一大批昆曲新秀崭露头角,受到昆曲界前辈的热情赞扬。会演期间,前辈艺术家作了示范表演,北方昆曲剧院、湖南郴州湘昆剧团的代表以及宁波昆曲的老艺人,也演出了各具特色的剧目。各路昆曲人马汇聚昆曲的故乡苏州,商讨艺术大计和培养接班人事宜,大欲进一步发展和繁荣昆曲事业。但紧接不久,就有“山雨欲来”的政治形势的突变。
“文革”前后的昆曲形势
“文化大革命”前的1964年,全国戏曲界提倡编演戏曲现代戏,作为古老剧种的昆曲,被看作是最难表现现代题材的剧种,不过昆曲在尝试编演现代戏方面跟其他剧种一样,也是比较早的。1958年,北方昆曲剧院首先排演了《红霞》,而后有浙江昆苏剧团的《寻宝记》、上海戏曲学校昆班的《海上渔歌》、湖南省嘉禾昆班的《钢铁火焰山)): 1959年,江苏省苏昆剧团也排演了《活捉罗根元》。这些新剧目的排演,仅是一种试验性的习作,都是不很成熟的作品,引起了戏曲界的讨论,有一种意见认为,昆曲还是擅长于表现古代题材。于是,在1960年至1963年间,昆曲重新编演了不少古代戏,主要的有上海戏校的《红楼梦》、上海青年京昆剧团的《白罗衫》,浙江昆苏剧团的《西园记》、《三关排宴》、《燕燕》,北方昆曲剧院的《文成公主》、《玉簪记》、《绣襦记》、《千里送京娘》、《五人义》、《雷峰塔》、《李慧娘》、《荆钗记》、《晴雯》,郴州专区湘昆剧团的《劫皇纲》、《夜珠公主》,等等。但是,从1963年起,戏曲编演现代戏已经形成热潮,昆曲也不例外,几乎新上演的全是现代戏,在当时影响较大的有北方昆曲剧院的《飞夺沪定桥》、《奇袭白虎团》,江苏省苏昆剧团的《黄海前哨》、《焦裕禄》,浙江昆苏剧团的《红灯传》、《芦荡火种》,上海青年京昆剧团的《琼花》,湖南省湘昆剧团的《腾龙江上》、《女飞行员》,等等。
昆曲自《十五贯》演出成功以来,十年间,事业得到了发展,演出不断,接班人也走上了舞台,而且成为昆曲演出的主要力量。昆曲的演出剧目除传统折子戏外,改编和创作了不少新剧目,其中既有古典名剧的整理改编,也有古代题材的新创作以及戏曲现代戏,已经形成了新中国昆曲的剧目格局。
但是,在1964年7月北方昆曲剧院的《李慧娘》被点名批判以后,昆曲的形势急转直下,很快就陷于覆灭的境地。“文革”期间,全国的昆曲院团先后被撤销。1966年,北方昆曲剧院被撤销;河北省京昆剧团被解散;江苏省苏昆剧团被撤销,苏州团改建为红色文工团,南京团改组为江苏省京剧团二团(1972年恢复江苏省苏昆剧团并撤回苏州);上海青年京昆剧团的昆剧队被撤销,1973年整团解体。1968年,永嘉昆剧团被撤销。1969年,湖南省昆剧团被解散(1972年恢复为郴州地区湘昆剧团);武义昆剧团与婺剧团合并而告终。
1976年,“文革”后,昆曲院团开始陆续恢复,最先重组的是永嘉京昆剧团,1979年撤京留昆,恢复永嘉昆剧团。1977年,浙江恢复浙昆,重组为浙江昆剧团;上海新建上海昆剧团;江苏重组江苏省昆剧院并调回南京,重组后的江苏省苏剧团仍留苏州,1982年恢复原名江苏省苏昆剧团。1979年,北方昆曲剧院恢复建制。1984年,郴州地区湘昆剧团正名为湖南昆剧团。昆曲学员班也恢复招生:1978年,浙江昆剧团招收“秀字辈”(后未以“秀”字排辈)新人,江苏省戏曲学校改称为江苏省戏剧学校并开设昆剧科招收学员,湖南省艺术学校湘昆科招生,浙江平阳开办永昆学馆招收新学员。1985年,湖南郴州地区艺术学校创办湘昆科并招生。1986年,上海戏曲学校招收昆三班学员。
“文革”后,全国共有七个昆曲专业剧院团,即北方昆曲剧院、江苏省昆剧院、江苏省苏昆剧团、上海昆剧团、浙江昆剧团、湖南昆剧团、永嘉昆剧团,除水嘉昆剧团于1991年后停歇活动外,其他六个院团也就构成今日中国昆曲演出团体的基本布局。
“文革”后的昆曲演出活动很快就恢复起来,并且举办了两大昆曲活动。
1977年,首先由浙江昆剧团复团演出了《十五贯》、《西园记》、《长生殿》,湖南昆剧团也恢复古装戏的演出,并移植了《逼上梁山》,江苏省昆剧院建院公演《十五贯》。
1978年,上海昆剧团也以《十五贯》作建团公演。最令人鼓舞的是,1979年北方昆曲剧院复院,《李慧娘》得以昭雪,隆重演出。全国各昆曲院团在恢复演出的同时,更重视院团之间的交流与学习,如1979年有浙江昆剧团与湖南昆剧团的联袂演出,江苏省昆剧院学习北昆《李慧娘》;1980年上海昆剧团学习北昆《晴雯》,也到郴州与湖南湘昆交流,接着湘昆还邀请“传字辈”和上海戏校的教师传授折子戏;1981年上海昆剧团应永嘉昆剧团之邀,派员支援排演新剧目;江苏省昆剧院邀请“传字辈”老艺人授戏。自1977年至1981年间,各院团接连创排新戏,如浙江昆剧团的《慰忠魂》、《难忘的一天》、《杨贵妃》,上海昆剧团的《蔡文姬》、《白蛇传》、《孙悟空三打白骨精》、《红娘子》、《烂柯山》、《钗头凤》、《白蛇传》、《唐太宗》,江苏省昆剧院的《关汉卿》、《吕后篡国》、《西施》、《朱买臣休妻》、《鉴湖女侠》,北方昆曲剧院的《桃花扇》、《血溅美人图》,永嘉昆剧团的《百花公主》等,初步形成交流演出折子戏和编演新剧目的局面。
1978年4月,三省一市昆曲工作者座谈会在南京举行,讨论昆曲艺术的继承和改革问题。昆曲在获得发展机缘的新形势下,第一次将继承和改革问题作为议题进行讨论。与会的浙江、湖南、江苏和上海的代表二百多人(北昆尚未复院,没有参加),广泛地就此重大问题发表了意见,认为继承与改革都很重要。主办单位江苏省昆剧院作汇报演出《十五贯》、《游园》、《狗洞》等,俞振飞、周传瑛、王传淞、郑传鉴、方传芸、倪传钺、邵传镛、张娴和湘昆雷子文等名家作了示范表演,有《太白醉写》、《贩马记》、《梳妆》、《上路》、《访鼠测字》、《寄子》、《刘唐下书》、《山亭》等。
1980年4月,在上海举行了“俞振飞演剧生活六十年纪念”活动,文化部、中国戏剧家协会的领导专程赴沪,上海及有关省市的文化领导和艺术家,以及京昆工作者和爱好者干余人出席。俞振飞演出了《太白醉写》,与张君秋合演《贩马记·写状》,祝贺演出有上海昆剧团的《断桥》、江苏省昆剧院的《痴梦》、浙江昆剧团的《写本》、湖南昆剧团的《醉打山门》、北方昆曲剧院的《干里送京娘》等。活动期间,举行了昆曲推陈出新座谈会,对昆曲的现状及改革与发展等问题进行了讨论,在肯定昆曲要“推陈出新”的基础上,俞振飞提出了改编昆曲古典名著的初步设想。
昆曲传习所成立六十周年纪念活动
1981年11月,“昆曲传习所成立六十周年纪念”活动在苏州举行。“传字辈”健在的十六位表演艺术家周传瑛、王传淞、姚传芗、沈传锟、包传铎、郑传鉴、方传芸、张传芳、周传沧、王传蕖、邵传镛、倪传钺、沈传芷、薛传钢、刘传蘅、吕传洪等虽年逾古稀,然皆精神焕发地参加了活动。这是对“传字辈”的纪念,也是对昆曲重视的一次盛会。文化部、中国文联、中国戏剧家协会、中国艺术研究院以及江苏、浙江、上海的文化界领导出席了大会,全国文艺界人士闻讯而至,与会人数达一千二百多人。
昆曲传习所,亦称昆剧传习所(参见上文),这次活动概称“昆曲传习所”。大会肯定和表彰了昆曲传习所和“传字辈”艺人六十年来对昆曲事业所作出的历史功绩,文化部向十六位“传字辈”演员赠送了纪念匾。大会还对昆曲艺术的推陈出新问题进行了专题的理论探讨,就抢救昆曲遗产达成了共识,确定了“统一规划,分散教学,集中汇报”的抢救、继承的方针。这是面对昆曲现实的正确的,也是关系到昆曲艺术发展的首要的方针。在讨论继承与改革的初期阶段,达成抢救昆曲遗产的共识,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这也是当年昆曲传习所以“传”字排辈的原旨。会议提出了“抢救、继承、改革、发展”的八字方针,并指出在贯彻“三并举”方针时,不搞一刀切,要照顾到昆曲的历史地位和艺术特点,既应该像《十五贯》那样推陈出新,保存优秀的传统剧目,也应该探索表现现代生活的途径。
大会期间,“传字辈”老艺人和俞振飞、张娴联袂演出了两台传统折子戏:邵传镛的《鸣凤记·吃茶》,郑传鉴、周传瑛、包传铎的《千忠戮·打车》,沈传锟的《风云会·访普》,倪传钺的《精忠记·交印》,周传瑛、张娴、包传铎的《鸣凤记·斩杨》,俞振飞、姚传萝的《玉簪记·琴挑》,刘传蘅、王传淞的《打花鼓》,周传沧的《探庄》,俞振飞、郑传鉴的《千忠戮·八阳》,刘传蘅、薛传钢的《渔家乐·刺梁》,沈传芷和青年演员张向澎的《长生殿·小宴》,还有青年演员张继青的《寻梦》,小演员张志红的《惊梦》等。同时有五场交流演出:上海昆剧团计镇华、华文漪主演的《钗头凤》,江苏省昆剧院张继青主演的《鉴湖女侠》,浙江昆剧团汪世瑜、王奉梅主演的《杨贵妃·惊变》和现代小戏《人情钱》,浙昆学员班的传统折子戏,江苏戏校昆剧科学员班的《哪吒》。
纪念活动结束后,江苏、浙江、上海两省一市的中青年演员掀起了学戏的热潮,由“传字辈”艺术家教授传统折子戏,“分散教学”活动非常频繁。
1982年5、6月,在苏州又举行了江苏、浙江、上海两省一市昆剧会演,与会代表来自全国及美国、法国、瑞士,有一千四百余人。会演“集中汇报”学戏的成绩,展示了昆曲中青年演员的艺术风貌,昆曲界又重新集结力量,将继承与振兴昆曲的使命落在建国后培养的第一、二代甚至第三代接班人身上。会演演出了三台大戏,上海昆剧团改编的《牡丹亭》、江苏省昆剧院按原著整理的《牡丹亭(上集)》、浙江昆剧团新编的《杨贵妃》,还有十台折子戏三十四出;俞振飞、郑传鉴、侯玉山、马祥麟等著名艺术家作了示范表演;永嘉昆剧团演员也参加了汇报演出。在会演中,一些知名的中年演员如计镇华、蔡正仁、华文漪、梁谷音、岳美缇、刘异龙、王芝泉、张继青、董继浩、范继信、汪世瑜、王奉梅等,表演艺术更见光彩,青年演员如石小梅、张志红、袁丽萍、胡锦芳、林继凡、陈同申等,也初露头角。会演结束,十六位“传字辈”老艺人获“荣誉奖”,江苏省昆剧院、上海昆剧团、浙江昆剧团、江苏省苏昆剧团获“继承革新奖”。会演期间,张庚、王朝闻作了有关学术报告,文化部就“推陈出新”问题再次召开了座谈会,重申了昆曲的“抢救、继承、改革、发展”的方针,还专题讨论了昆曲音乐的改革问题。这次会演,进一步推动了昆曲传统剧目的抢救、继承工作,也促进了昆曲艺术的继承与革新的研究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