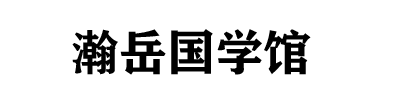昆曲历史:五、进入折子戏的时代
雍正、乾隆年禁外官置备家班
这一时期,清皇朝的中央集权统治进一步加强,在保持满洲mjn贵族统治地位的前提下,笼络汉族官僚士大夫,在中央机构实行满汉复职制度,地方知府以下官吏主要由汉族充当,进一步完善科举制度,但是对官吏,特别是对汉族官吏和士子的管束更为严厉,文武生员如有赌博挟妓者,从严究治,比常人罪加一等。雍正即位后“整纲纪”,于雍正二年(1724年)就“禁外官畜养优伶”,“家有优伶,即非好官,着督抚不时访查”,凡现任官僚不得置备家庭戏班。雍正七年(1729年)革除教坊,改设“和声署”,以“廓清宇宙”。可是乾隆年间,又有“买歌童之事”发生,所以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又重申禁令,《高宗实录》记载谕旨曰:“联恭阅皇考谕旨,有伤禁外官畜养优伶之事。圣训周详,恐其耗费多金,废弛公务,甚且夤缘生事,救督抚不时防查纠参,虽一二人,亦不可徇隐……若再不知警悟,甘蹈罪愆,非特国法难宽,亦为天鉴所不容矣。”禁令虽针对任官,然缙绅士大夫亦有所收敛,置备家班的明显减少了。《清稗类钞》曰:“雍、乾间,士夫相戒演剧,且禁蓄声伎。至于今日,则绝无仅有矣。”清《锡金识小录》亦说:“本朝乡绅,较前明远胜……未为有害如前明之沈酣声色,广取艳妓妖童者无有也。”
禁令虽严,但禁任官不禁缙绅士大夫,禁官吏家班不禁演戏,演剧之风仍很兴盛。官吏家班被遣散,人数不少,大多加入到民间职业戏班,且那时候北京、苏州等地已有戏馆,尤其在苏州,“不论城内城外,遍开戏园,集游惰之民,昼夜不绝,男女混杂”,民间演剧随戏园的发展而更趋旺盛,大吏豪富也兴起叫“堂会”的风俗。乾隆南巡时,两淮盐务也“例蓄花雅两部,以备清唱”。雍正朝不过十三年,禁官吏家班之令对昆曲的发展并未有多大的影响,只是自此以后家庭戏班日益减少,而民间的职业戏班却得到了大发展的机遇。
昆曲创作的末路和清宫大戏
自康熙末经雍正朝到乾隆年,再也没有出现清初的苏州派剧作家群体和康熙年间的“南洪北孔”昆曲传奇的创作高潮,实际上从康熙中叶开始,传奇创作已经在走下坡路了。雍正、乾隆年间,昆曲传奇的创作无外乎两种倾向:一是粉饰太平的“供御”之作,二是脱离生活、脱离群众、脱离时代的“风雅”之作。这两种倾向,势必走入穷途末路。这时期,大多数作家作品并没有多少价值,而稍有可观的如夏纶、张坚、黄之隽、金兆燕、李斗等诸剧作亦为少数,而唐英、杨潮观、蒋士铨、沈起凤等作家作品,在当时影响较大。自这时期以后,昆曲剧本的创作在案头剧的路上越走越远,在昆曲舞台上没有留下什么剧目,所以本著略去不述。
唐英,辽宁沈阳人,汉军正白旗出身。乾隆初年在九江关任上时聘张坚为幕僚,熟悉昆曲。所作传奇十七种,名《古柏堂传奇》。他的昆曲作品大多为当时流行的地方戏曲的改编,如《巧换妻》、《梁上眼》、《双钉案》、《十字坡》、《三元报》、《梅龙镇》、《面缸笑》、《芦花絮》、《天缘债》等,都是江西、安徽一带地方戏常演剧目。他将原属梆子、秦腔、乱弹班的戏改作昆曲来唱,并且在戏中还保留部分地方声腔,这样可以争取更多的普通观众,可谓有胆有识。
杨潮观,江苏无锡人,五十岁后长期在四川任邛州知州,晚年回原籍家居。在邛州任上,得卓文君妆楼旧址,筑吟风阁,其杂剧三十二种名《吟风阁杂剧》。他是著名的短剧作家,每做一种,即“传之金石,播之歌声,假伶伦之声容,阐圣贤之风教”,作品充满封建说教。杨为官比较清正,同情民间疾苦,虽亦为陶写性情,但也有比较好的作品,结构简洁,主题清晰,文笔清新,如《穷阮籍醉骂财神》、《贺兰山滴仙赠带》、《魏徴破笏再朝天》、《韩文公雪拥蓝关》、《寇莱公思亲罢宴》,其中《罢宴》一折传唱至今,成为昆曲的保留剧目。
蒋士铨,江西铅山人,官至翰林院编修,诗文与袁枚、赵翼齐名,称“三大家”。他是乾隆年间最著名的剧作家,作剧多种,以《藏园九种曲》传名,包括传奇六种,杂剧三种。他的作品除《香祖楼》外,基本上是就事写剧,缺少艺术的提炼和虚构,没有多大的普遍意义和生命力。因是诗人写剧,剧作的曲文清新洒脱,如写汤显祖的《临川梦》传奇和据白居易《琵琶行》诗所写的《四弦秋》杂剧,情词俱佳,很得文人的欣赏。
沈起凤,江苏吴县人,是乾隆中叶影响最大的剧作家。所作词曲不下三四十种,风行于大江南北。乾隆南巡时,曾被命为扬州盐务和苏、杭织造备写供御之戏。剧作《红心词客四种》为《才人福》、《文星榜》、《伏虎韬》、《报恩缘》,在当时很著名。他作品的特点是,以苏州地区的社会生活为背景,文字用苏白,描写的是社会上的各种职业、身份的各色人物,性格鲜明,语言逼肖,情节有趣,有很好的剧场效果,在当时很受观众欢迎,但是作品立意不高,格调较低,后来也就慢慢地消声于舞台。
乾隆年间,正是“太平盛世”,出现了编演“清宫大戏”的热潮。所谓的“大戏”,是指其演出规模空前,剧本篇幅冗长,结构荒诞离奇,旨在维护封建统治、宣扬封建迷信的作品。康熙年间,宫廷就设“南府”,专事音乐和演剧,雍正七年(1729年)曾被改为和声署,至乾隆七年(1742年)设“乐部”,专司奏乐,戏曲承应仍恢复“南府”的称名。南府分“内学”与“外学”,内学指宫廷里学戏的太监,外学指应召的民间梨园界的艺伶,外学既教内学,也演戏,名为“承应戏”。
乾隆年间,外学人数遽增,演出每本大戏,就需百数十人。据清昭琏《啸亭续录·大戏节戏》,乾隆初,命张文敏专司大戏剧本,以供演习。宫中大戏各有名目,按各节令奏演的谓《月令承应》,应内廷诸喜庆事奏演祥瑞谓《法宫雅奏》,于万寿令节前后奏演群仙神道谓《九九大庆》,以上为仪式礼节庆贺排场;又有演故事的,演目连救母事谓《劝善金科》,演唐玄奘西域取经事谓《升平宝筏》,演三国典故者谓《鼎峙春秋》,演宋梁山诸事者谓《忠义璇图》等。这些作品皆出于“游客之手”,又抄袭元明流行诸剧本。“大戏”每本有百余出、数百出,演出之时,呈戏之人无虑数百。清赵翼曾看过“大戏”的演出,在其《簷曝杂记·大戏》条说,“内府戏班子弟最多,袍笏甲宵及诸装具,皆世所未有”;而其所演之戏,“取其荒幻不经,无所触忌,且可凭空点缀,排引多人,离奇变诡作大观也”。这种“大戏”,皇亲国戚不过是见人见景看排场,若没有有趣的情节和高超的表演艺术,常看便会索然无味,因此在故事性的“大戏”中抄袭来的民间的流行折子戏,如《山门》、《北饯》、《回回》、《思凡》、《下山》等,得以保留,也是幸事。
宫廷除了演“大戏”,也演昆曲折子戏。据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立册的南府《穿戴提纲》第二册中,记载了三百十二出昆曲的穿戴,其中虽然极大部分折子戏在康熙朝时就有演出,但在乾隆年间也是常演的剧目,其中不少属于《西游》、《三国》、《水浒》戏的著名折子戏,而如《琵琶记》、《荆钗记》、《拜月亭》、《南西厢》、《牡丹亭》、《浣纱记》等著名传奇的折子戏则更多,这也说明乾隆年间折子戏盛行,宫中演剧亦是如此。乾隆十六年(1751年),皇帝第一次南巡江南,因喜欢昆曲,回銮时,即带回江南昆班中男女角色多名,隶入南府,谓之“新小班”,此后更陆续征召昆曲艺人晋京入宫。乾隆年间,“新小班”和原在南府的大班、小班昆伶集合起来,人数很多,住景山内垣,苏州梨园供奉所居,俗称“苏州巷”。南府和景山两处有关演出的人员,多至一千四五百人,规模极为庞大。乾隆十六年(1751年)皇太后六十寿辰和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皇太后七旬庆典,所举行的盛大庆典演出,就是由内府承应供奉的。
这时期,文人创作“屏绝俚鄙”,追求其“雅”,蔚成风气,这就逐渐与普通观众疏离;宫廷演剧,原设昆、弋两部,而特重昆曲,官吏富商也以观演昆曲为“雅”事。于是,昆曲也就被尊称为“雅部”了。但是,昆曲自得“雅部”尊称以后,却预示着一种可悲的结局。稍有例外者为数很少,如《雷峰塔》。
关于《雷峰塔》传奇
乾隆年间最有影响的作品是《雷峰塔》传奇。这是一部取材于民间传说,描写蛇仙白娘子爱情故事的传奇。这部传奇的形成有着特殊的过程,其间,民间艺人和昆班的加工演出起着主要的作用,《雷峰塔》因此广泛流传于昆曲舞台。
白蛇的故事在南宋时就已广为流传,明编《清平山堂话本》就收有宋人词话《西湖三塔记》。元邾经曾作《西湖三塔记》杂剧,未见流传。明中叶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亦记有此故事。冯梦龙编《警世通言》,也有《白娘子永镇雷峰塔》一回。陈六龙据此故事编撰过《雷峰塔》传奇,祁彪佳《曲品》认为它很不成功。
百年之后,约在乾隆三年(1738年)出现了黄图珌的《雷峰塔》传奇。黄图珌,江苏松江人,除《雷峰塔》外,还作有《栖云石》传奇和《南曲》四卷。其《南曲》中有《观演雷峰塔传奇》一文,云:“余作《雷峰塔》传奇凡三十二出,自《慈音》至《塔圆》乃已。方脱稿,伶人即坚请以搬演之。遂有好事者续‘白娘生子得第’一节,落戏场之窠臼,悦观听之耳目,盛行吴越,直达燕赵。”“黄本”突出白娘子的温柔多情和对爱情的执著追求,表现了许宣性格中的动摇成份。作者从封建正统观念出发,否定这种爱情婚姻,结局以白娘子被镇于雷峰塔下、许宣皈依佛门而告终。但此剧在实际演出中,却如上文所说,“好事者续白娘生子得第”,以肯定这种爱情婚姻的观点进行了改编,并在戏场广为流传。原因有二:一,“白娘生子得第”,符合观众的欣赏心理,所谓“与世情合”;二,增补了《端阳》、《盗草》、《水斗》、《断桥》、《产子》、《祭塔》等重要的关目,凡三十六出,突出了白娘子对人间爱情的忠贞与追求,以及对阻碍这种追求的势力的斗争精神。相传,进行这种改编的是扬州内班的著名伶工陈嘉言父女,且以乾隆初期“梨园抄本”或称“旧抄本”流传。“梨园抄本”的影响显然远比“黄本”要大。
“梨园抄本”在长期的演出中,又不断得到修改提高,逐渐趋于相对稳定中。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方成培在“梨园抄本”的基础上,保留其精华,加强了人物性格和悲剧性冲突,改定为三十四出本。方成培,安徽新安人。 他在改本《雷峰塔》的“自序”中说:“余于观察徐环谷先生家,屡经寓目,惜其……辞鄙调讹……因重为更定,遣词命意,颇极经营,务使有裨世道,以归于雅正。较原本曲改其十之九,宾白改十之七。《求草》、《炼塔》、《祭塔》等折,皆点窜终篇,仅存其目。中间芟去八出。《夜话》及首尾两折,与‘集唐’下场诗,悉予所增入者。”可见方成培改本除增删关目外,主要在曲白上进行了较大的改动,且改曲多于宾白,“以归于雅正”。
乾隆年间作剧求“雅”,并不是一条正确的途径。又因为“梨园抄本”在舞台上演出已久,所以,在实际的演出中,“方本”的改动并没有被接受多少。但方成培在对情节结构和关目的增删,以求完整,以及修改曲词以合音律方面,功绩亦不可没。《雷峰塔》传奇在不断被修改和以“梨园抄本”为基础这点上,可以说是一种集体创作。它在舞台上流行最久的折子戏是《盗草》、《水斗》、《断桥》三折。
进入折子戏竞演的时代
昆曲传奇自《长生殿》、《桃花扇》以后,再也没有出现特别优秀的作品,为数不多的作家作品片面追求“雅”,有的作品仅为个人情怀的抒发,有着案头剧的倾向,除了《铁冠图》、《雷峰塔》和沈起凤等人的作品,还能在戏场流行外,也只能归入所谓的“传统剧目”了。昆曲的剧目,自明嘉靖、隆庆之前的一部分南戏改唱昆腔到嘉靖、隆庆时的《浣纱记》、《鸣凤记》,再到清康熙时的《长生殿》、《桃花扇》,已有大量的积累。在长期的演出中,特别是明末清初以来,有的优秀折子已经成了常演的剧目,因此自康熙末经雍正朝到乾隆中叶,昆曲的演出已经进入了折子戏竞演的时代。在这时期,全本戏中的部分折子经过历代艺人的多次加工提高,逐步形成昆曲折子戏的独特的表演艺术体系,大量的折子戏在广场、戏馆、厅堂等场所演出,使昆曲走向另一种性质的繁荣,即表演艺术高度的发展和折子戏演出的繁荣。
折子戏要脱离全本戏而成为独立演出的单元,必须经历一番长期的演变过程。它的形成过程非常复杂。有一种说法,在明万历末已有在宴席演戏时“插一出”的习俗,这是事实,明袁中道《游居柿录》中就有记录。但当时还没有“折子戏”的概念。在演戏必演全本或节本的年代,选出若干散出演出,这在明末已经存在。如明张岱《陶庵梦忆》所记:“天启三年,余兄弟携南院王岑、老串杨四、徐孟雅、圆社河南张大来辈往观之……剧至半,王岑扮李三娘,杨四扮火工窦老,徐孟雅扮洪一嫂,马小卿十二岁扮咬脐,串《磨房》、《撇池》、《送子》、《出猎》四出,科诨曲白,妙入筋髓,又复叫绝。”很明显,这是曲友、串客串戏,在私家厅堂偶尔为之。这四出戏后来成为《白兔记》的主要折子戏。明末祁彪佳的《日记》中也有一些看散出戏的记载:如崇祯五年(1632年)有“观演戏数出”之类的活动,有时把散出戏称为“杂剧”。崇祯十二年(1639年)十月十四日在钱德舆家,“德舆尽出家乐合作《浣纱》之《采莲》剧而别”。可能钱氏家乐演《采莲》有特别的风格,所以特地演给同好欣赏。后来,《采莲》也是《浣纱记》常演的折子戏。
诸如此类的演出全本戏中的散出,在明末清初已经渐渐多了起来。这时期,出现了几种特别标明“昆腔”名目的戏曲选本,最有代表性的是《醉怡情》。这是由明末青溪菰芦钓叟编辑的,当时就有明末崇祯年间的原刻本,后来又有清初重刻本,共八卷。全书选录了元明两代南戏、传奇的散出,收录了明末在戏场流行的昆曲折子戏,每种四出,如《琵琶记》之《剪发》、《贤遘》、《馆逢》、《扫松》,《占花魁》之《一顾》、《再顾》、《种缘》、《狂窘》,《牡丹亭》之《入梦》、《寻梦》、《拾画》、《冥判》,《玉簪记》之《窃词》、《阻期》、《逼试》、《送别》等四十四部作品的一百七十六个单出,其中四十三种一百七十五出为昆曲折子,另有一出为弋阳腔《孽海记》之《僧尼会》,也即后来改唱昆曲的《思凡》、《下山》。但是,戏的出目还不稳定,跟文学本和以后的舞台流行出目仍有不同。
到康熙初叶,社会上演出折子戏已经有了风气。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康熙皇帝南巡到苏州,驻跸行宫(今拙政园),曾去祁工部衙门用饭听唱昆曲,戏班上演了《前访》、《后访》、《借茶》等二十出,这二十出戏都属折子戏无疑。至于宫廷南府档案《穿戴提纲》所载三百十二出昆曲折子戏穿戴。这档案册子虽是乾隆年初期造写的,但这些折子戏也是康熙年经常演出的剧目。那时,已经有串演部分折子或选择各本的折子组成一台戏演出的两种形式了。宫中如此,在地方上也是如此。在观众对全本戏的故事已很清楚的情况下,这种可以自由组合折子、讲究表演质量的演出形式,很自然地得到了观众的欢迎。所以自康熙以来到乾隆中叶,折子戏的演出渐成气候,昆曲已经进入了折子戏竞演的时代。
雍正至乾隆中叶,折子戏的流行和职业昆班的发展也是相互联系在一起的。
自明以来,苏州演唱昆曲之风一直很盛,至清乾隆年也许更为兴盛。采自民风的《苏州竹枝词》有歌“中船唱戏旁船酒,歇在山塘夜不开”,“千金浪掷爱名优,多买歌童拣上流”,“家歌户唱寻常事,三岁孩童识戏文”云云,演唱昆曲已经成为生活内容之一。据清顾公燮《消夏闲记》:“至雍正年间,郭园始创开戏馆,既而增至一二馆,人皆称便。”苏州的第一家戏馆即“郭园”。后来发展很快,至作者写作《消夏闲记》的乾隆五十年(1785年)时,金阊商贾之地竟有数十处,遂有官家禁馆之举,但禁后所留也有十数家之多。这些戏馆演戏兼卖酒菜,吴语称“拉正”。从此,职业昆班有了比较固定的演出场子。
苏州的职业昆班很多,其行会组织“梨园总局”,设在城内镇抚司前的老郎庙,康熙时已由苏州织造府掌管。苏州织造府以供奉宫廷丝绸织造为主,兼管梨园,要为南府选送色艺俱佳的昆曲艺伶,皇帝南巡时还要组织著名昆班供奉唱戏。雍正十一年(1733年)府下也置备有昆班“织造部堂海府内班”(时任织造监名海保,故称海府)。这是一个地位特殊、规模很大、演剧水平很高的职业昆班。名旦吴福田、名老生朱文元曾任该班总管,拥有优秀昆伶三十五人,承应官场演剧。乾隆南巡时,该班供奉演剧,演员乐师曾达百余人。它还成立了苏州历史上最早、规模最大的海府串班,班中有陈应如、费奎元、汪颖士等著名串客。
据清钱泳《履园丛话》:“余七八岁时,苏州有集秀、合秀、撷芳诸班,为昆腔中第一部。”钱泳生于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他七八岁时正当乾隆三十一二年,这时的“集秀班”被史家称为“老集秀班”。清吴长元《燕兰小谱》亦说乾隆三十年以来有集秀班,即指“老集秀班”。集秀班的名气很大,广东、江西、安徽、湖南等地都曾利用过这块“名牌”,乾隆后期金德辉的昆班也由“集成班”改称“集秀班”。但是关于老集秀班和合秀、撷芳诸班的资料很少,无从知其详情。若参照生活在康熙、雍正时代的吴敬梓的《儒林外史》小说,那时昆班演出的大多是《请宴》、《窥醉》、《借茶》、《刺虎》、《思凡》之类的折子戏。《儒林外史》虽然说的是南京,但苏州也应是如此,除了有限的新作外,演得多的也是折子戏。清赵翼诗云“焰段流传本不经,村伶演作绕梁音”,所谓“焰段”,就是借宋杂剧语指昆曲折子戏。
那时的扬州也是昆曲盛演之地,清郑板桥《扬州》诗云:“画航乘春破晓烟,满载丝管拂榆钱。千家养女先教曲,十里栽花算种田。”扬州与苏州有地理相近之利,在昆曲的联系上甚为密切。扬州城内有条街即取名“苏唱街”,梨园总局就设在此街的老郎庙。扬州成了苏州昆曲的第二故乡。清金埴《不下带编))卷七有诗云:“从来名彦赏名优,欲访梨园第一流,拾翠几群从茂苑,千金一唱在扬州。”即说苏州(茂苑)昆伶名优到扬州一唱而红,能得到“千金”之酬,十分风光,扬州人称之为“兴虫”。这种关系保持了很久,乾隆南巡时更为热闹。
扬州的昆班也很多,活跃在雍正、乾隆年间的“维扬广德太平班”就享有盛名。该班曾流动演出于安徽广德一带,简称“太平班”。艺伶为苏州人,班主不详,成员极多,行当齐全,演员五十二名,另有教习七名、场面二十一名。乾隆第二次南巡到扬州,该班也御前承应,精排昆曲折子戏十八出接驾,如《星聚》、《仙集》、《献瑞》之类的仙佛戏,《笏圆》、《请郎》、《劝农》之类的太平戏,还有一出《女长亭》,即《南西厢·长亭》,全由女伶扮演,以博新奇娇美。班中有非常著名的苏州艺人王九皋,后来加入扬州老徐班,晚年回苏州。
乾隆年间,扬州极为繁华,亦多昆曲名班,有所谓“七大内班”。这是两淮盐务为接驾专门组织的昆班,都由盐商置备,虽说是家班,但要听从盐务衙门的差遣,不能擅出扬州,其演出功能与职业昆班无异,被称为“内江班”。按其成立先后有老徐班、黄班、张班、汪班、程班、洪班、德音班。这里先述首倡者“老徐班”的情况,其余各班在下文再述。
扬州盐商徐尚志从苏州聘来昆曲演员,组成昆班,阵容整齐,角色亮丽。徐班开启了乾隆年间扬州昆曲剧坛的繁荣局面,后人称之为“老徐班”。乾隆十六年(1751年)皇帝第一次南巡,扬州盐务局命老徐班供奉演戏。该班有演员二十多人,擅演剧目数十本,表演水平极高,行头档次亦高。平时该班为主人自娱,皇帝南巡时接驾供奉,也可在扬州城乡作营业性的演出。演员各有擅演的折子“看家戏”:老生山昆璧,身长七尺,声如洪钟,演《鸣凤记·写本》,观者视为“天神”;小生陈云九,年九十,演《吟诗脱靴》,风流横溢,人称“化工”;老外孙九皋,以身段见胜,首创《荆钗记·上路》的舞蹈动作;白面马文观,兼工副净,以《河套》、《参相》、《游殿》、《议剑》诸出擅场;小旦许天福,演“三杀”(《杀嫂》、《杀惜》、《杀山》)、“三刺”(《刺汤》、《刺梁》、《刺虎》),世无可比者。当时的名伶已经开宗立派,如董派小生董美臣,擅演《长生殿》,其徒张维尚,以《西楼记》擅场,人称“状元小生”。名演员以擅演的折子戏而享其盛名,在社会上影响很大,观众亦已养成挑艺人、挑剧目看戏的习俗。
从这时期起,除苏州、扬州外,昆曲的演出在各地的情况有所不同,因为地方声腔的兴起对昆曲的地位是有很大影响的。
如北京,一直处在戏曲声腔杂陈的局面,但昆曲却始终存在。雍正十年(1732年)北京《梨园馆碑记》载有戏班十九部,其中玉秀班、秀雅班疑是昆班。乾隆十五六年(1750、1751年)有昆班庆成班、宝和班,前者可能是个女子昆班,后者疑是“保和班”的同名异写。保和班是乾隆中叶的北京名班,早期是高腔、昆腔的合班,后期渐以昆曲名重京都。清《百戏竹枝词》反映了乾隆二十年(1755年)北京有吴音、弋阳腔、秦腔、乱弹腔、唱姑娘、四平腔等,“吴音”即昆曲水磨调,那时也出现“伧父殊不欲观”的情况。宫中演剧的情况已如上述,例有昆、弋两部。
清代其他地区的昆曲亦不如明代远甚。如南京的昆曲,自入清以后未能恢复繁荣,但仍有苏州艺人到南京落户的,清捧花生《画舫余谭》说,有原籍苏州金阊的小伶朱双寿,驰声梨园,所演《絮阁》、《藏舟》、《打番儿》、《雪夜琵琶》诸折子戏,令“观者莫不心醉”。又有庆丰班和太晟班也有演出。昆明地区,据会馆碑记,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前后,有桂林班、金升班、金玉班、秀雅班、荣和班、玉林班等戏班的演出,其中秀雅班很可能就是昆班。还有官府中的几个“小班”,如广州地区,昆曲作为“外江班”,只在官僚士大夫之间还有点位置,在社会上就不如本地的“潮音”受人欢迎。清绿天《粤游纪程》记有,雍正十一年(1733年)前有桂林独秀班到广州演出,亦能昆腔苏白,与吴优相若。又有郁林土班,可唱得“不昆不广”,能戏也不多。到了乾隆年间,随着丝绸商贸的发展,外省戏班也有不少到广州来演出了,各种声腔剧种都有,其中也有昆班,如“姑苏红雪班”等。到乾隆后期,“外江班”则更多,昆班亦随之有增加。
昆曲折子戏的演出,要到乾隆后期和嘉庆年才达到高潮。而在雍正、乾隆中叶,昆曲正处在一个转折期,苏州、扬州地区演出繁荣,其他地区还在发展之中,但已经形成风气。实际上,从乾隆中叶起,社会上已经开始出现规模较大、影响深远的编集昆曲折子戏的选本。
全面反映乾隆中叶折子戏的面貌和时代特色的选本,就是清钱德苍编集的十二集本((缀白裘》。早在明末就有玩花主人的编选本《缀白裘》,在康熙、雍正年间又出现过同名的折子戏选本,钱德苍根据玩花主人旧编和当时舞台流行的折子戏,陆续收辑,重新编集。自乾隆二十八年至三十九年(1763-1774年),每成一集,即由钱德苍在苏州开设的宝仁堂印行,特题名为《时兴雅调缀白裘新集初编》。钱原编为十二编,后来在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由四教堂翻刻,改为十二集,以卷数标目。这部新编本很快风行各地,大受欢迎,成为昆曲爱好者的必备之书。作为舞台演出本的新集《缀白裘》,得到如此广泛欢迎,不断翻印,正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这时期昆曲折子戏的流行情况。《缀白裘》,是“取百狐之腋,聚而成裘”的意思。犹有折子戏一个专名谓“摘锦”,意思是“摘”一本传奇之“锦”,后来各种杂出都可谓之“摘锦”,《缀白裘》中也沿用了这个名称。收入的流行折子戏是从/又十八部作品中选取的四百三十出,另外还兼收了总题为“梆子腔”的地方戏三十余种五十九出,编为十二集四十八卷。此书被认为是流行于乾隆年间的昆曲折子戏的“大戏考”,后来近现代所能演的昆曲折子戏,大抵不出这个范围。《缀白裘》的编集问世,结束了昆曲史的第二个二百年,它具有某种划时代的意义:它标志着昆曲全本戏演出的衰亡,进入折子戏演出趋向兴盛的新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