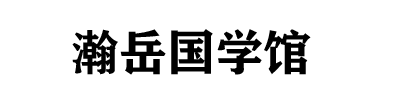昆曲历史:六、乾嘉传统的形成
昆曲在“花雅之争”中失去独尊的地位
“花部”指各地的地方声腔,实际从明代以来一直在发展着,如弋阳腔、秦腔和民间小腔等。康熙时,作为“花部”的地方声腔已有了发展的势头,到了乾隆年间特别地兴旺起来,才构成了对昆曲的竞争态势。自清初昆曲被称为“雅部”起,“花部”诸腔已在慢慢地形成与昆曲的抗衡之势。“花雅之争”的过程,实际是昆曲与“花部”诸腔互相交流、吸收的过程,昆曲之失,在于它失去了独尊的地位,出现了“纯粹昆班”与“昆乱同班”并存的局面,昆曲的地位在降低,昆曲的影响在消衰。同时,“花部”诸腔之间也存在着竞争与消长的关系。
乾隆年间,“花雅之争”在扬州与北京存在着明显的较量。乾隆南巡到扬州,“两淮盐务例蓄花雅两部以备大戏。雅部即昆山腔;花部为京腔、秦腔、弋阳腔、梆子腔、罗罗腔、二簧调,统谓之乱弹。”(清李斗《扬州画舫录》)扬州的昆曲艺人基本上是从苏州来的,那时扬州的昆班有势力很大的“七大内班”与“太平班”,而“花部”被称为“外江班”,尽管有春台、丰乐、朝元、永和等班,以及乾隆后期来的四喜班等,但势力还是难敌昆班。而在北京情况就不同了,早在乾隆九年(1744年),就有市民“所好惟秦声、罗、弋,厌听吴骚”的现象。乾隆四十九年,檀萃写《杂吟》诗云:“丝弦竞发杂敲梆,西曲二簧纷乱咙,酒馆旗亭都走遍,更无人肯听昆腔。”在乾隆中后期,花部崛起,昆曲将衰,已成趋势。在北京,昆曲与京腔、秦腔,昆曲与徽班,这前后两次最有代表性的较量,就决定了作为“雅部”的昆曲的最后败局。
在北京的弋阳腔早已被称做“高腔”,后来形成京腔,乾隆年间已出现“六大名班,九门轮转”的极盛状况,与昆曲抗衡,挫弱了昆曲的势力。乾隆中叶,已经强盛起来的秦腔流布全国,各地秦腔艺人集结北京,成为京腔与昆曲的强劲对手。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四川秦腔艺人魏长生入京,以《滚楼》一出,“大开蜀伶之风,歌楼一盛”,色艺俱胜京腔,京腔六大班遂无人问津,京腔艺人不得不附入秦班,一时“京、秦不分”,秦班压倒京班,成为北京最有影响的剧种,再一次动摇了昆曲在北京的地位。这时候的北京昆曲除了“纯粹昆班”外,已经有了京、秦、昆的同台演出,如宜庆、萃庆等京腔班有昆曲折子戏的演出,魏长生的秦腔永庆部也有昆旦锡龄官和李秀官。就是“纯粹昆班”保和班,在乾隆末年分为文班和武班,武班已杂有许多花部剧目,多唱吹腔、拨子。
弋腔在各地皆有变种,京腔原是弋阳腔在北京的变种,所以也被统称“弋腔”。据《钦定大清会典事例》,乾隆五十年(1785年)议准禁止秦腔戏班演出,本班艺人,概令“改归昆、弋两腔”,或者“另谋生理”。后来,魏长生也就南下,不久回四川去了。据胡忌考,在昆、弋、秦三腔同台演出中,所谓的“乱弹腔”是一种非昆非梆、亦昆亦梆的声腔,这在清《百戏竹枝词》中被称为“昆梆”,是以筝笛伴奏的一种新声腔。它不是梆子腔,也不是昆腔,而是昆曲传统中名之为“吹腔”的声腔。在《缀白裘》中题名为“乱弹腔”的《阴送》、《挡马》,前者唱[急板乱弹腔],后者唱[披子](或谓[批子])。在长期的“昆调乱弹”戏的声腔混合中,形成了乾嘉时期的吹腔系统,于是在昆曲中也就出现了吹腔或吹腔剧目。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变化,当然也会影响到南方的昆曲。
事隔两年之后,徽班进京又揭开了北京“花雅之争”的新的一页,竞争更为激烈。那就是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皇帝八十寿辰,由高朗亭率领的第一个徽班三庆班从扬州晋京祝寿。三庆班以唱二黄调为主,兼唱昆曲、吹腔、四平调、拨子,诸腔并奏。三庆班入京,很快压倒秦腔,秦腔艺人大多投入徽班谋生,形成了徽、秦二腔合流。继三庆班之后,又有四喜、春台、和春各徽班进京,改变了北京剧坛的面貌。这就是著名的“四大徽班进京”。因秦腔又名甘肃调,甘肃调一名“西皮调”,这次的“徽秦合流”在声腔上初步形成以二黄、西皮为主的诸腔同台并奏的局面。徽班中的昆曲也不在少数,如春台班能演《拾画》、《冥判》、《见娘》、《孙诈》、《惠明》、《小逼》、《扫秦》、《弹词》、《闻铃》等昆曲折子戏,而四喜班本以唱昆曲为主,清《梦华琐簿》云:“四喜曰曲子,先辈风流,饩羊尚存。”据嘉庆中期《听春新咏》,记录了徽班能演昆曲三十三出,基本上是昆班常演剧目,如《藏舟》、《刺梁》、《佳期》、《拷红》、《偷诗》、《茶叙)).《裁衣》、《戏叔》、《相约》、《讨钗》、《楼会》、《水斗》、《断桥》、《思凡》等,估计能演的还有不少。
道光初年,北京专唱昆曲的仅“集芳”一部,不少昆曲戏已在徽班之中了。徽班在扬州耽了较长时间,其中艺人籍贯为江苏的占了三分之一,也有苏州人,嘉庆以后安徽人增多,“吴儿渐少”。如春台班,嘉庆时苏、皖艺人大体相等,到道光年安徽籍艺人已超江苏籍,而且又增加了湖北籍艺人。因为道光年间,湖北艺人王洪贵、李六、余三胜等进京,带来了楚调之后,又引起了一场新的变化,促成了湖北西皮调与安徽二黄调的第二次合流。楚调亦称“汉调”,所以这次的变化被称为“徽汉合流”,并度为新声,皮黄腔由此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这就再一次削弱了昆曲,使昆曲成了“花部”的附庸。到了咸丰年后,皮黄腔在北京已经兴旺发达,完全取代了昆曲的地位,结束了昆曲独尊数百年的局面。
在南方折子戏演出继续繁荣
前文只说到乾隆中叶的昆班和昆曲折子戏的盛演状况,从乾隆南巡一直要延续到乾隆后期,南方的昆班和昆曲折子戏的演出继续在走向繁荣。而且在康熙、乾隆年间流布的基础上,昆曲也继续在西南、西北存留着影响。乾隆中叶以后,昆曲虽然受到了花部诸腔的冲击,动摇了独尊的地位,但在南方仍有势力,在其他地区亦仍有影响。
在陕西,素来流行秦声,乾隆四十年(1775年)严长明到西安也对秦声发生了兴趣,但他仍看到在陕西为官的对昆曲很熟悉,如王文治不仅写昆曲剧本,还置备有家班。在秦腔的吹奏曲牌中保留有昆曲牌子,在东路戏中也有唱几大段昆曲的《渔家乐》。而陕西的皮影戏,其腔调不与秦声近,反与昆曲相近,也可以说是所谓的“昆梆”。据清佚名的《观剧日记》,乾隆五十九年至六十年(1794-1795年),甘肃、宁夏也有昆曲的踪影。兰州有“秀元部”擅演《断桥》、《合钵》,宁夏有严三虎擅演《佳期》。清梁章钜《浪迹续谈》说他在道光初年任甘肃布政使时,适萨湘林将军过访,两人不约而同地点演昆曲,“非《思凡》即《南浦》”。在西北地区官僚依旧置备家班,当然,这已不会是纯粹的昆班了。
在广州,来粤的外江班很多。据胡忌考,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来粤的有安徽保和班和湖南集秀班,五十六年(1791年)来粤的有苏州的十一个戏班和湖南普庆班,可能全是昆班。乾隆以后,昆曲仍不绝于粤东。在昆明,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老郎宫碑记上即刻有“富大人东院内班”、“谭大人西院内班”之名,这两个“内班”基本上也是昆班。当地在同时期有“阳春部”,据清檀萃《梨园宴和歌》诗与序,阳春部是由安徽先生带去昆明的小班,称“七部第一”,那么,其他六班也可能是昆小班了。阳春部这次演戏二十三出,除少数为其他声腔,大部分为昆曲,如《扫花》、《三醉》、《脱靴》、《惊梦》、《惊丑》、《琴挑》、《借茶》等。这已是乾隆年间受花部影响后昆班演出的惯例了。
在江南昆曲故乡苏州、扬州的情况就不同了。
乾隆中叶,苏州原有很著名的老集秀班和海府内班。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苏州重修老郎庙立有碑记,合郡梨园有昆班集秀班、聚秀班、结芳班等三十九部,大多以“秀”字名班,隶属以上各班的主要艺人有王九皋、赵乾初、蔡茂根等苏州籍艺人一百九十八名。这样的昆班规模,反映了苏州昆曲演出繁荣期的面貌。“集秀班”名列众班之首,这是规模最大、水平最高的,为承应翌年乾隆第六次南巡而组织的新班社。据清龚自珍《书金伶》一文记载,四十九年乾隆六十岁南巡,江南的织造、盐运使都在争聘名班准备接驾,两淮盐运使正为此事发愁,艺人金德辉就献一策,说:“小人请以重金号召各部,而总进退其短长,合苏、杭、扬三郡数百部,必得一部矣。”两淮盐运使大喜,即命金德辉组班。金德辉组织了三郡的名伶,组成了这一高水平的昆班。承应供奉演出后,乾隆皇帝大喜,问起班名,答曰:“江南本无此班,此集腋成裘也。”后来“驾既行,部不复析,而宠其名曰集成班,复更曰集秀班”。集秀班是这一时期最有代表性的昆曲班社,活动达半个世纪之久,到道光七年(1827年)才最后报散。
清吴长元《燕兰小谱》说:“集秀,苏班之最著者,其人皆梨园父老,不事艳冶,而声律之细,体状之工,令人神移目往,如与古会,非第一流不能入此。”集秀班班首闺门旦金德辉,擅演《题曲》、《寻梦》,沈起凤称其表演“冷淡处别饶一种哀怨”,人称“金派声口”。小生李文益、小旦王喜增串演《折柳·阳关》,“情至缠绵,令人欲泣”。旦色王三林演《赏荷》“幽娴贞静”,演《金山寺》“软款轻盈”。也有色美而艺未精的旦角张蕙兰,昔在保和部演《思凡》颇为众赏,以捐金谋入该班,止能扮演杂色。集秀班在嘉庆年初期曾进京演出,为适应京城时尚,却以年轻的旦色居多。清《日下看花记》云:“此部初自南来,闻风者交口赞美,则旦色之佳,有以动人也。是日亮台,座客极盛。”但北京的昆曲已在衰落之中,该班进京演出也没能起多大的作用。
扬州的昆曲演出,仍以“七大内班”为主,规模都很大,所演剧目多是为人熟知的传统折子戏。前文已经介绍了乾隆中叶的老徐班情况,据清李斗《扬州画舫录》,其他六班的昆曲演出,在民众中的影响也很大。如老黄班三面顾天一,以演武大郎擅场,所以通班就演《义侠记》,人人争胜,遂获盛名。老张班的老外张相国工小戏,擅演《拆书》、《惠明寄书》,年近八十演《宗泽交印》,神光不衰。又有老生陈元凯的《写本》、刘天禄的《弹词》、三面顾天祥的《羊肚》和《盗甲》、小旦马大保的《醉归》等。老汪班情况不详。老程班的大面冯士奎以《刘唐》擅场。老旦王景山眇一目,上场用假眼睛如真眼。大洪班的孙九皋,年九十余尚能演《琵琶记·遗嘱》。又有老生周星如的《骂曹》、白面张明诚的《罗梦》、二面恶软的《鲛绡记·写状》等。老江班的小生石蓉棠与朱冶东演《梳妆·跪池》,风流绝世。又有小生董抡标的柳梦梅、大面范篙年的铁勒奴、蔡茂根的法聪等,皆令人叫绝。“七大内班”中身怀绝技的名伶很多,他们的演艺以及在观众中受欢迎的程度,也代表了乾隆、嘉庆时期昆曲艺术的特点及其发展的情况。
此外,女子昆班也很活跃。扬州有著名的女子昆班“双清班”,初居小秦淮客寓,后迁芍药巷。班主是苏州人顾阿夷,有女伶十八人,其中也有佼佼者。如喜官唱《寻梦》是金德辉唱口;金官演《相约相骂》,如出鬼斧神工;康官演《痴诉·点香》,满座叹其痴绝;四官能唱大花面,演《闹庄·救青》之铁勒奴,神似老江班的名净范篙年。班中有个男正旦许顺龙,是教师的儿子,也在班中串戏,玉官演《南浦嘱别》的蔡伯嘈,许扮赵五娘,人称“生旦变局”。
苏州、扬州昆曲演出的盛况,也可以从当时的昆曲工尺谱集《纳书楹曲谱》得到反映。《纳书楹曲谱》的编辑校订者是当时著名的清曲家叶堂,苏州人,名医叶天士之孙。叶堂唱曲法度甚严,得吴江徐氏之传,后又传之钮匪石,所谓“叶派唱口”,几乎成为习曲者的最高准则。他与丹徒王文治合作编订了《纳书楹曲谱》十四卷。乾隆五十七年至五十九年(1792-1794年)刻成全书。书成,风行一时,号为“叶谱”。卷首有乾隆五十七年叶堂自序,云:“究心于此者垂五十年,而余亦既老矣……自《琵琶记》以降凡如干篇,都为一集;又徇世俗所通行者,广为二集。”叶堂在“凡例”中一再说明,选收“家弦户诵,脍炙人口”之昆曲折子戏,为使演出者方便,俗名与原本不同者一律从众。叶在订正曲谱上很严格,而在选收剧目上均为当时演出的场上之曲。全谱正集四卷、续集四卷、外集二卷、补遗集四卷;所收剧目,不计散曲十二种,有北曲杂剧三十六折,南戏、传奇二百九十四出,时剧二十三出,共计三百五十三出戏。《纳书楹曲谱》反映了乾隆后期昆曲舞台常演剧目的概貌,演出的几乎全是传统折子戏。它与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编定的《缀白裘》相比较,所收剧目大体一致。
乾嘉传统与苏州风范
乾隆、嘉庆时期,在昆曲的表演艺术史上有着特殊的意义。这一时期,在竞演折子戏的舞台实践中,演出水平不断得到提高,在与花部的较量中,昆曲积累了很丰富的演出经验,更注重在演艺上精益求精,自明以来积累的丰富经验,又通过几代艺人的努力,最终形成了影响深远的昆曲表演艺术的传统。这个传统,可以称之为“乾嘉传统”。它主要包括:以折子戏为表演艺术的基础,包括对折子戏的加工、提高,更适宜于舞台表演;职业昆班空前活跃,使昆曲表演深入民间;唱、念、做表演上重视规范,表演体制趋于相对稳定;同时也重视表演艺术的传承延续。
以折子戏为主要演出形式,全面推进了表演艺术的发展。这时期的昆班在前人常演剧目的基础上,从传统剧目中精心选演折子戏,对家喻户晓的剧目进行加工、提高,特别讲究表演艺术,以期引起观众的欣赏兴趣。艺人的演出本叫“梨园本”,是一种对文学本的“改本”,艺人通过动结构、删人物、重穿插、详细节、规范表演,甚至在无戏处造戏等手段编成“梨园本”,这些都是为了演出的需要。艺人依靠自己丰富的舞台生活经验和表演经验,以及聪明过人的智慧和绝技,使折子戏的演出取得极佳的舞台效果,促进了表演艺术的发展。
职业昆班的演出也处在一种相互竞争的社会环境中,名伶名戏名班的社会效应对于职业昆班的生存和发展至关重要,艺人必须不断提高演艺水准。当时苏州的“集秀班”和扬州的“七大昆班”都以名伶名戏为组班的基础,相当重视技艺和表演经验的积累,注重唱功技巧和摹状写情的细腻,而且不特重旦之艳色,那时也很重视“串客”的“客串”,清客也常搭昆班演出。这些串客大多是演艺过人者,如老旦费坤元和老生陈应如,初在海府串班,后入大洪班;余蔚村,能读经书,解九宫谱,为老徐班首席副末;扬州盐商巨富江鹤亭,他家的串班扬州第一。历来的串客多具有学问,对声腔、音律、戏情、戏理、妆扮、身段等有较深的研究,各擅其门。他们参与昆曲活动,把昆曲的表演艺术推向更完美的艺术境地。
艺人精心设计表演,以演技使人物生辉,在表演上十分严格,表演手法愈来愈丰富,唱、念、做的格式渐趋规范化,并相对定型。如弋腔的《下山》改唱成昆曲后,充满南方情调;《芦林》改唱昆曲后,生扮姜诗改为付扮,越发迂腐可爱,并借用弋本起句“步出西郊”,使人物出场更具个性。《燕子笺》惟以一出《狗洞》流传,也是由原文学本《奸遁》改来,改成了以说白神情表演为主的付丑戏,止留一曲以身段表演的[桂坡羊],留一白面门官陪衬,一冷一热,相互烘托,刻画尽鲜于信做不出文章的丑态。《南西厢·长亭》俱用旦色妆扮,名为《女长亭》。《惊梦》出十二花神,创造堆花舞蹈,以诗意表现梦中欢会;《琴挑》修改插白,设计一连串的身段动作,精致细微地表现潘必正的少年情怀。此类创造性的格式规范举不胜举。集秀班最能体现乾隆、嘉庆时期的昆曲表演艺术的优秀传统,如金德辉的《题曲》、《寻梦》,被视为“金派”,他们不仅演艺达到最高水平,而且演剧作风严谨。该班讲究功夫和经验的积累,重艺不重色,注重唱和表演的独创性。他们在舞台演出中恪守规格,被称为“苏州风范”。扬州老徐班的艺伶也是“苏州风范”的表率,老外孙九皋创造《上路》的身段舞蹈动作,小旦许天福“三杀三刺”的表演程式,小生董美臣的董派唐明皇,大面周德傅的铁勒奴、楚霸王、张将军,白面马文观的曹操等,名家迭出,其艺递传,演出的格式及其表演的科段遂成规范。
据清《扬州画舫录》,这时期的昆曲脚色行当,昆曲称“家门”,已基本趋于定型,共分“十二脚色”:“梨园以副末开场,为领班。副末以下老生、正生、老外、大面、二面、三面七人,谓之男脚色;老旦、正旦、小旦、贴旦四人,谓之女脚色;打诨一人,谓之杂。”而后只是具体细致地根据人物形象和生活经验再加以细分而已。家门的齐备和发达,也标志着表演艺术的规范化,各家门都有特别吃重、累功的戏,行话叫“正场”或“五毒”。表演艺术渐趋规范、定型,无论唱念做功,都有严格的标准。唱有准绳,以叶堂“叶派”为正宗,有《纳书楹曲谱》传其宗;作为做功的表演身段和动作,有古代惟一的总结演艺心得的《明心鉴》和记录身段谱的《审音鉴古录》。
据吴新雷考,《明心鉴》为乾隆年间的苏州昆曲宗师吴永嘉原著,杜双寿抄存,书室名“瑞鹤山房”。原著四卷,卷首有无名氏“原序”,序曰:此书“先生为后学之子弟指示迷津,苦心良可见也”,旨在“以心为鉴,明益求明”,故曰《明心鉴》。实际上,《明心鉴》是历代艺人的演艺经验总结,不可能出自个人的创造。卷一,指出了昆曲唱与做的“毛病十六症”。卷二,提出了唱念方面咬字吐音的治病秘诀。卷三最为重要,专讲昆曲表演艺术的技巧和方法,如“八形象”,要辨角色的“老、少、文、武、醉、癫、贫、富”之八种形象;“四色分”,要分“喜、怒、苦、惊”之四色状,分心中“欢、恨、悲、竭”之四色声;又有“面做状,眼先引”、“头摇点,肩落兴”、“手为势,脚宜蹲”之类的表演技法。卷四有声、曲、白等十六个条目,综合解说昆曲的唱与做的各种问题。此书对当时及后来的昆曲表演艺术都是弥足珍贵的演艺理论。
《审音鉴古录》是昆曲折子戏的身段谱。清无名氏编辑,王继善订定,虽然存世的是道光十四年(1834年)的刊本,但其记录的身段表演是在昆曲表演基本定型的基础上编成的,应该是可以反映乾隆、嘉庆年间昆曲表演规范和水平的。如《荆钗记·上路》,唱[八声甘州]时的身段,就是由孙九皋传下的。全书收录昆曲折子戏六十六出(实为六十五出),对角色的穿扮、表情、身段和舞台调度的设计,都有具体而详细的提示。其中《琵琶记》十六出、《荆钗记》八出、《红梨记》六出、《儿孙福》四出、《长生殿》六出、《牡丹亭》十出(《堆花》一出有目无文,实为九出)、《南西厢》六出、《鸣凤记》四出、《铁冠图》六出。
苏州昆班的昆曲,以其严谨的演艺作风、重艺不重色的准则,以及在穿戴、表演上的严格标准,形成了为人所称道的“苏州风范”。
重视师徒传授、流派师承,以使昆曲的表演艺术代代相传,这一传统也是相当重要的。清李斗《扬州画舫录》中记载有这方面的许多例证。在乾隆、嘉庆年间群芳竞艺中,尤其在“家门戏”的表演中,妆扮穿戴、表演风格、唱曲口法及小腔运用等各方面各有特点,形成不同的流派,显示了师承传授的传统。如老生陈义先一派传徒朱文元再传陈元凯,余维琛一派传刘天禄,张德容一派传王采章;老外王丹山一派传倪仲贤;小生陈云九一派传石蓉棠,董美臣一派传子董抡标传徒张维尚再传徒沈明远;大面周德傅一派传徒范篙年再传徒奚松年,马美臣一派传陈小扛,马文观一派传徒王炳元;三面陈嘉言一派传婿周君美;正旦史菊观传任瑞珍再传徒吴仲熙、吴端怡;二面钱云从称“钱派”,姚瑞芝、沈东表则人称“国工”;小旦吴福田有“无双唱口”之称,金德辉则人称“金派唱口”。乾、嘉时期仅苏州、扬州一带,就呈现流派纷呈的局面,故表演艺术在竞争中趋于顶峰,也在情理之中。
综上所述,可知乾嘉传统的精神实质和表现的内容,它对昆曲表演艺术体系的形成有着决定性的意义。
昆曲在流布地区形成的支派
明万历年后,昆曲就流布各地,数百年来,昆曲在其流布地区渐渐与地方声腔发生了密切的关系。这是一个长期的缓慢的互相消长的关系。昆曲吸收着地方声腔的营养,也会与地方声腔同台演出,昆曲对地方声腔发生着影响,也会被地方声腔吸纳,发生变化而成为地方声腔系统中的成份,表现出与苏州地区的昆曲不同的特点,成为昆曲的“支派”。昆曲对地方声腔的影响,延续的时间很长。自乾隆、嘉庆年间的“花雅之争”后,昆曲在全国的势力同样会受到削弱,有的慢慢地销声匿迹,有的则成为了所谓的“支派”。形成各地“支派”的时间有先后,时间跨度也大,主要在19世纪的道光至光绪年间,为叙述方便就放在一起说了。可以称为“支派”的,有北昆、浙昆、徽昆、赣昆、湘昆和川昆。
浙昆:昆曲在浙江流布极广,以杭、嘉、湖为中心,旁及金华、丽水、绍兴地区,然而只有浙东之“永嘉昆曲”和“宁波昆曲”可视为支派。温州古称永嘉,是宋元南戏的发祥地,又是海盐腔的流行地区,明万历年间,昆腔传入永嘉。清乾隆年后曾一度衰落,道光年后便见复兴,有著名昆班同福班和品玉班。至晚清,乃是永嘉昆曲的中兴时期,昆班不断涌现,最多时达三四十个,又有新同福、新品玉等名班。永嘉昆曲多穷生戏,地区特征明显,演出风格粗犷、质朴,生活气息浓郁。以温州方言和中州韵结合的土官话为舞台语言,曲牌组合和唱腔旋律变化不大,但不用赠板曲,不作切音,节奏较疾速,小生用本嗓,在表演上别具一格。宁波昆曲,习称“草昆”或“甫昆”。昆曲最迟在明末清初传入四明地区,因明张岱《陶庵梦忆》说,调腔女戏朱楚生“其科白之妙,有本腔不能得十分之一者”,“本腔”者,即宁波人称为“昆曲本班”。至清咸丰年间,甫昆兴盛,班社林立。同光年间,著名的昆班有“上三班”之老庆丰、新庆丰、老聚丰,“五公座”之老凤台、老绪元、老景荣、老三绣、大庆丰,人才济济,名角众多,各有看家好戏。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后开始衰落,渐趋消歇。甫昆后期剧目多武戏,其演艺风格为“昆曲笛子,调腔锣鼓,做工考究,话音带土”。曲牌唱腔虽不失昆腔韵味,但速度较快,且兼演调腔剧目,谓“开调”与“不开调”,长期“昆调参演”,昆味减弱。
徽昆:据明潘之恒《亘史》,昆曲传入安徽当在明万历年间。万历以来,在宣城、徽州、青阳、池州、安庆一带已出现昆腔与徽州腔、青阳腔等同台演出的情况,并出现众多的题名“时调青昆”、“徽池雅调”、“昆池新调”、“南北官腔”等戏曲选本,呈诸腔杂陈的面貌。清乾隆、嘉庆年间,徽班吸收了不少苏州、扬州的昆伶,兼演昆曲,有正昆与徽昆之区别,徽昆受诸腔影响,常用方言土语,以唢呐与大锣大鼓伴奏,风格粗犷,擅演武戏。清乾隆年后,皖南徽班就以昆腔与吹腔戏为多;首先进京的徽班三庆班,有旦角陈桂林,擅演《盗令》、《游街》、《学堂》、《思凡》、《拷红》、《戏叔》等,全是昆曲。因长期由徽班兼演,徽昆的表演艺术受吹腔的影响,如四喜班以演昆曲为主,能演昆曲剧目很多,然其演唱的却是以石牌腔(俗名吹腔)为主。道光年后,徽班在激烈的竞争中,终于“尽变昆曲”而改唱西皮、二黄,京剧诞生后,徽昆也就渐趋消歇。
赣昆:昆曲掺入赣剧,最早是清初的玉山班,清乾隆以前本地区昆曲的影响不大,活动范围仅限子南昌、九江、赣州等城市,只在家班活动,嘉庆以后昆班活动就显著减少。清中叶以后诸腔活跃,渐渐形成高腔、乱弹、昆曲合流的赣剧,赣昆只作为支派保留在赣剧中。在光绪二十八年至二十九年(1902一1903年),婺源洪福林昆班被乐平秧坂马家接管,改名万春班,又从浙江金华、兰溪聘请部分艺人,演出昆曲剧目。另外,广信班的昆曲是由安徽传来的,曲调比较丰富。赣昆戏目不多,唱法不甚讲究,吐字多方音土语,地方色彩强烈,演出风格大方爽朗,除武戏较完整外,大多在弹腔戏中“雨夹雪”唱若干昆曲片断;在东河戏、宁河戏、抚河戏中也有这种情况,可以说是“昆乱同台”。
湘昆:约在明隆庆、万历年间,昆曲就已传入湖南,在明代基本上是家班演出。据“长沙老郎庙班碑”和清江宾谷《潇湘听雨录》,清初长沙仍有昆班演出。康熙年间,刘献廷在衡阳看到“楚人强作吴歈”,这时昆曲已带有地方色彩了。乾隆年间,曾有长沙普庆班和桂阳(今湖南郴州)集秀班到广州演出。昆曲传入湖南后,影响很大,有许多专业班社长期演出昆曲,以桂阳为甚。咸丰、同治年后,有不少苏州昆曲艺人入湘,使湖南的昆曲不断得到充实。当时著名的昆班有昆文秀班、福昆文秀班、胜昆文秀班等十多个班社,流行于以桂阳为中心的湘南一带。至同治、光绪年间,昆曲渐衰。所谓“湘昆”主要是指“桂阳昆曲”。湘南称昆班为“文秀班”,所以昆班多以“文秀”命名。桂阳昆曲宾白参用弹腔白口,付、丑不作吴语,改用地方语言。因受祁剧、湘剧的影响,桂阳昆曲在表演艺术上形成自己的特点,虽保持了昆曲细腻优美的风格,但也创造了不少饶有山野乡土风味的表演程式,柔中见刚,且吸取了民间歌舞,湘南色彩浓郁。唱腔旋律朴实无华,曲调进行略快,以湖广音为舞台语言,且有滚唱、滚白,形成了具有地方特色的“俗伶俗谱”。
川昆:昆曲入川时间也晚,有说在清顺治、康熙年间,那时只是由入川的江苏昆伶坐唱。但较可靠的是同治、光绪年间有“舒颐”昆班的演出(见《蜀海丛谈》卷三《吴勤惠公传》),是四川总督吴棠招苏州佳伶组班的。一说此是后期舒颐班,而前期舒颐班在乾隆年间就已有了,是由坐唱班发展而来的。舒颐班在嘉庆年时有名丑彭四,名旦曾双彩、屈玉凤等,道光十八年(1838年)时又有大面周浩然,其子周辅臣生净兼长,父子擅演昆曲剧目甚多。清末民初,舒颐班解体,四川不复有昆班了。舒颐班活动时间很长,其与地方艺人交流甚密,如川班的岳春、萧遐亭、罗开堂、傅三乾、彭华廷、蒲松年等名家皆习昆曲而闻名。昆曲流入川班后,很快被“川化”,苏白变成川白,除少数折子戏仍唱昆腔外,大多已以“风绞雪”的形式与高腔等声腔合流,成为川剧“昆、高、胡、弹、灯”五大声腔之一。
北昆:昆曲自明万历年间进京成为玉熙宫大戏,并成为“官腔”以后,江苏昆班不断上京,至明代后期也曾盛极一时。至清康熙年间,因皇帝提倡,昆曲又一度复兴,不仅在“南府”供奉,而且士大夫蓄家乐,民间也有昆班。清中叶之前,京中昆班大多系江南子弟,其在表演艺术上乃宗苏州昆曲一脉。清中叶乾隆、嘉庆而后,情况就发生变化,“花部”诸腔相继进京,作为“雅部”的昆曲就此衰落下去,而后出现“昆、弋合流”和“昆、黄合流”两种趋势;至道光年间,昆、弋同班演出方式向河北中部、东部一带发展,并与当地艺人结合,逐渐形成了北方昆曲“昆弋”一派,与南方昆曲长期并存,于是“昆”有南北之分。“昆、黄合流”的结果,昆腔逐渐被强盛起来的皮黄戏所吸收和融化,包括它的剧目、音乐和表演;又因为皮黄戏毕竟是从南方传入的,“昆、黄合流”仍带有南方色彩,未能形成北派。“昆、弋合流”则不同,江西弋阳腔在明代传入北京,结合京音与北方曲调,又在河北地区流传,早已北方化了,被称做“京弋腔”。明代北京的昆腔还带有南方的特点,可流传至清代中叶,受弋阳腔影响,已逐渐发生变化。“南府”组建“外学”,招收北方子弟习昆曲,免不了带有“北味”;又京弋腔能唱南、北曲目,甚至能唱昆曲剧目原本,唱念悉依“中原韵”。
乾隆以来,昆、弋同班已成习俗,昆曲的唱念表演已融入了弋阳腔的风格和手法。当时昆、弋班的艺人,“南府”和“外学”都能昆、弋兼擅。直至清末,昆弋艺人代有名伶,京中的“庆”、“荣”两辈和冀东的“益”字辈,成为昆弋派的骨干,一直发展到近代的“荣庆社”,以及后来的“祥庆社”,北方昆曲一派已形成深厚的基础和有别于南方昆曲的演艺传统。
“昆、弋合流”的结果形成了“北昆”。北昆的势力虽然强大,但已不是原产江南的昆曲了。北昆唱念基本上用北方语音,演员大多出生于河北,乡音重,但吐字归韵仍守昆曲规律;因受弋腔影响,具有高亢、刚健、饱满、奔放的演出风格。北昆演出剧目以袍带戏为多,且能擅演源于北杂剧的十余折北曲折子戏,较多保留有风格火爆的武戏;在昆腔润腔方法上与传统昆腔润腔有细腻的变化,并且,奏南曲牌子与唱南曲牌时有用“乙、凡”二音。较之南方昆曲同源而异流,二者韵味不同,情趣各异,是昆曲北方化的一支劲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