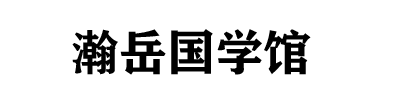昆曲历史:二、四方歌曲必宗吴门
以苏州为中心向周边地区及南北方流布
这时期的昆腔已不再局限于“吴中”一带,它以苏州为中心向外扩展蔓延,经魏良辅、梁辰鱼等人改造过的昆山腔,在苏州地区已具备了较扎实的基础,曲家和平民很快地接受了新腔,流行地区必然要向周边蔓延,而且愈传愈远,在流传的过程中又会得到不断的加工和提高,虽然会略有变化,但更丰富了唱腔艺术。正如明王骥德《曲律》所说:“昆山之派,以太仓魏良辅为祖。今自苏州、太仓、松江,以及浙之杭、嘉、湖,声各小变,腔调略同。”这些地区原来就有海盐腔和昆山腔并茂的基础,所以接受新腔很快,由于地区不同,在苏州地区之外“声各小变,腔调略同”,也是很正常的事。明潘之恒《鸾啸小品》就说“无锡媚而繁,吴江柔而淆,上海劲而疏”,水磨调在周边地区的唱腔风格也会有所差异,而在流传到较远的江苏常州以北、浙江嘉兴以南地区后的腔,潘之恒称之为“逾淮之橘,入谷之莺”,更远的地区则变化会更大,因为它必然会受到该地的原有声腔和方音的影响。
尽管如此,昆腔新声在流传之中影响越来越大,万历中期,士大夫蓄家乐成风,在无锡、常熟、松江、上海等地竞演昆腔,而且也出现了职业戏班流走江湖、传播昆腔新声的新局面。如明冯梦祯《快雪堂日记》所记,在万历三十年(1602年)就有“吴徽州班”在安徽曾演出《玉合记》、《义侠记》,“旦张三者新自粤中回,绝伎也”。这就是说在安徽和广东已都有昆腔演出。湖南地处昆曲南传广东和西南去广西、云南的要冲,万历中期昆腔即传播到此,其时,龙膺中年回湖南武陵家居时,作《诗谑》,有诗云“腔按昆山磨颡管,传批《水浒》秃毫尖”,他在家中不仅演过许自昌的《水浒记》,还曾演出自己的作品《金门记》。据明顾起元《客座赘语》记载,在万历以前南京的公侯与缙绅及富家,平时在宴会、小集时,多用散乐,或三四人,或多人,唱大套北曲;若逢喜庆节日,则演北曲杂剧,即唱演北曲四大套。万历以后,受昆腔新声的影响,不演北曲,而尽演唱“清柔而婉折”的南曲昆腔了。昆腔在被称为“南都”的南京发展很快,而且职业戏班的竞演也非常热闹。这时,南京和繁华的扬州成了昆腔演唱的另一个“中心”。
在万历后期,昆腔就传到了北京,那里也“尽效南声”了。明王骥德《曲律》说:“入我明……始犹南北画地相角,迩年以来,燕赵之歌童舞女,咸弃其捍拨,尽效南声,而北词几废。”所谓“南声”,即指“吴中”的昆腔。在北京的官宦之家和宫廷都有了昆腔的演唱。
据明袁中郎《游居柿录》的记载,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后,他曾在北京的极乐寺左国花堂和姑苏会馆,看吴伶演《白兔记》、《八义记》,也有官宦被感动得痛哭欲绝;到了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在“魏戚畹园”也看到官宦“招名优演《珊瑚记》”。北京演唱昆腔,在明《祁忠敏公日记》中更有具体的记载。从明沈德符的《万历野获编》等著作中,可以知道宫廷演唱昆腔的较为详细的情况。明宫廷有专门为演戏所设的玉熙宫,演习“外戏”,弋阳腔、海盐腔、昆山腔皆备有,近侍有三百余人,承应宫廷演出。明末清初著名诗人吴伟业《琵琶行》诗云:“先皇驾幸玉熙宫,凤纸金名唤乐工。苑内水嬉金傀儡,殿头过锦玉玲珑。”宫中已常演昆腔戏。明史玄《旧京遗事》说“外戏,吴曲本戏也”,指的就是昆腔全本戏,在宫中还有昆腔教师何明,皇亲达官家还有无锡邹氏家班中星散流入京中的一流的生、净老伶人;阳武侯薛氏家诸伶中也有吴江旦色,所以说“今京师所尚,一以昆腔为贵”。但是,万历年间昆腔入京,当时在民间还没有多大的影响,这跟江南地区普遍传唱昆腔的情况有所不同。
昆腔新声的传播推动清唱随之风行
魏良辅等人改革的昆腔新声,专在清唱上求“闲雅整肃,清俊温润”,曲唱“时曲”,所谓唱“冷板曲”。学魏良辅唱时曲之风气,早在嘉靖末就从苏州地区向周边蔓延,这种蔓延,起初也主要是指清曲的唱。“清唱”比起“剧唱”来,要求更为严格,有许多清规戒律,原来只是清曲家的歌唱艺术,隆庆、万历以后,随着昆腔新声的广泛传播,平民百姓也能随口清唱几段名曲,清唱曲风行起来,清曲家的地位也随之而提高,他们的清唱活动对于提高昆腔艺术和普及昆腔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
当时的清唱活动,一般在家庭宴会和苏州虎丘曲会上演唱。明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引松江民谚,说清唱“起于苏州,波及松江,二郡接壤,习气近也”,称不知腔板的“游手好闲之人”痴迷于昆腔清唱者为“清诳”,所谓“游手好闲之人”,大多是指城市平民、各行业手艺人、贩卒舆夫,民谚描绘了他们十种痴狂的形态。当时的诗人袁宏道还写了首《江南子》,诗云:“蜘蛛生来解织罗,吴儿十五能娇歌。旧曲嘹历商声紧,新腔啴缓务头多。一拍一箫一寸管,虎丘夜夜石苔暖。家家宴喜串歌儿,红女停梭田畯懒。”这些,都很形象地反映了万历年间昆腔清唱的普及程度。
万历年以来,清曲家随着清唱的风行也就多了起来,而且成分也复杂多了。大致有三类人:文人墨客、医生及中小地主和富商,他们有文化、有财力、有时间,懂音律,肯钻研,享有不同程度的声誉;原来就是民间的清曲家,为了谋生以教唱曲为业,称为“拍曲先生”;官宦豪富之家,为卖弄风雅也学些唱曲装点身份,不求甚解,实际还称不上清曲家。
这一时期著名的清曲家大多是继承嘉靖、隆庆时的曲师的衣钵而享盛名的,如魏良辅的再传弟子纽少雅和及门弟子周似虞等,有以度曲名闻四方的徐君见、精于审律的朱学隆、《牡丹亭》唱曲家云间道人徐氏等。当时,有的清曲家被缙绅人家请去教曲,时称“清客”,纽少雅与徐君见就曾做过清客。徐君见与写《板桥杂记》的余怀交好,余怀称其“年六十余,而喉若雏莺静女”,“按拍一歌,缥缈迟回,吐纳浏亮,飞鸟遏音,游鱼出听”,他还培养了一批青年唱曲家。朱学隆曾点定袁于令的《西楼记》,《西楼记》之曲流传市井巷陌也有他的功劳,吴伟业有诗赞其“自是风流推老辈,不须教染白髭须”。云间道人唱《牡丹亭》曲,就是老曲师也难能挑剔。当时很多缙绅豪富之家都养有家班,清曲家也常常成为这些人家的座上客,并为其家班优伶教曲。他们是以曲会友,志趣相投,所谓的清客也是很受人尊敬的。据明冯梦祯《快雪堂日记》,原是嘉靖时苏州邓全拙弟子的黄问琴在冯家一再清歌,并与著名戏曲家臧晋叔论词谈曲,相处甚洽。另据明钱谦益《似虞周翁八十序》,周似虞以医士身份与贤士大夫交游,常轻衣骏马,应名士酒会。
随着清唱的风行,嘉靖年已有明文徴明手书的魏良辅《南词引正》流传,万历年始还刻印了许多曲选,当时最著名的就有《吴歈萃雅》(附《魏良辅曲律》)、《吴骚合编》、《群音类选》等,刻印曲选的传统一直延续到明末和清中叶,其中也有其他声腔的曲选,但昆腔曲选占了很大的比重,为普及和提高昆腔的唱演起了很大的作用。
苏州的虎丘曲会既是群众性的唱曲活动,也是清曲家施展歌喉的良机和新剧目展演的场所,昆腔新声所以能取得成功,就因为它能很快在群众中传播开来,这跟虎丘曲会的习俗也是有一定的缘由关系。虎丘曲会大约在明正德、嘉靖年间就开始有了,一直延续到清乾隆、嘉庆年间,前后盛行达三百年之久。然而,在隆庆年间苏州府曾立石禁约,除士大夫、住持僧外,“荡子挟妓携童,妇女冶容艳妆”,禁游虎丘。只是在这短时期内未见有虎丘曲会的记载,后来此禁也就自然失效了。
苏州人习唱昆腔的风气开得很早,养成了每年八月中秋聚集在虎丘唱曲的习俗。据明李诩《戒庵老人漫笔》,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中秋,有青年周仕在虎丘唱曲“吴歈冠绝一时”,有倡女张少华和歌,技出周上,其后周仕吹箫,张少华唱曲,听者自觉不及。那时,正是魏良辅改革昆山腔的时期。魏之传人周似虞也年年要在虎丘唱曲,钱谦益诗云“此翁少好游,游兴老不衰”,是个唱曲高手。
在万历年间,一年一度的虎丘曲会曾出现过盛况空前的雄伟场面。明袁宏道《虎丘》一文说,“从千人石上至山门,栉比如鳞,檀板丘积,樽罍云泻”,刚开始唱时,有“唱者千百,声若聚蚊”,后来“竞以歌喉相斗”。竞唱活动延续到月明时,犹有三四人和歌,“一箫一寸管,一人缓板而歌”,比至夜深,箫管也不用了,有“一夫登场,四座屏息,音若细发,响彻云际”,“飞鸟为之徘徊,壮士听而下泪”。这最后一人就是此番竞唱之优胜者。
稍后的明张岱在《陶庵梦忆·虎丘中秋夜》中描述得更为详细:“虎丘八月半,土著流寓、士夫眷属、女乐声伎、曲中名妓戏婆、民间少妇好女、患子娈童及游冶恶少、清客帮闲、傒僮走空之辈,无不鳞集”,山上的每一处地方都坐满了人,“登高望之,如雁落平沙,霞铺江上”。当天色暗下来月亮上升时,“鼓吹百十处,大吹大擂,十番饶钹”,“雷轰鼎沸,呼叫不闻”,然后,鼓钱声渐渐停歇,丝管奏起来了,就开始万人齐唱同场大曲,有《浣纱记》中的“锦帆开,牙墙动,百花洲,清波涌……”和“澄湖万顷,见花攒锦绣……”作为竞曲的序幕,可谓热闹非凡。然后竞曲开始,直到夜深,人人放喉歌唱,“南北杂之,管弦迭奏”,随之有曲家的评论和群众的议论,赛出优胜者数十人而已。到二更鼓时,其他的管弦乐器被撤去,只留“洞箫一缕,哀涩清绵”,与清柔婉折的唱曲声相回旋,这时场上仅有三四人更番竞唱了。半夜三更时,天气转凉,许多人兴尽而散,最后一位曲师高坐石上,不用箫也不用拍板,“声出如丝,裂石穿云”,听曲者“不敢击节,惟有点头”。这时,端坐聆听者犹有百十人。这种景象,也只有在万历年的苏州虎丘山才能一遇。
除一年一度的赛曲外,新编的传奇也会拿到虎丘千人石上演出,以扩大影响。万历中,嘉兴有个屠宪副曾于中秋的晚上,率领家班在虎丘演出卜世臣的新作《冬青记》,“观者万人,多泣下者”,这样的场面令人惊叹。在明代的一些传奇中,如《荷花荡》、《金钿盒》、《秋虎丘》,也有有趣的虎丘曲会的描写,明沈宠绥的《度曲须知》也有一篇《中秋品曲》,专门评价了虎丘曲会上清曲家的唱曲。
万历年开创了昆腔传奇的时代
万历年前,创作的昆腔传奇不多,昆腔所演唱的大多是南戏剧本,或根据南戏改编的剧本。自嘉靖、隆庆以来,随着昆腔新声的流行和《浣纱记》传奇的成功,以及万历年清唱的风行和家班、职业戏班演剧活动的频繁,文人墨客创作昆腔传奇的渐渐多了起来,昆腔传奇的创作很快就打开了新局面,进入了繁荣期。这时期,作家作品层出不穷,作家的风格和流派渐次形成,创作和演出的繁荣促进了昆曲艺术的进一步发展。
明王骥德《曲律》说:“今则自缙绅、青襟,以迨山人、墨客染指为新声者,不可胜纪。”明吕天成《曲品》也说:“博观传奇,近时为盛。大江左右,骚雅沸腾,吴浙之间,风流掩映。”明沈宠绥《度曲须知》则更以“曲海词山,于今为烈”来形容“名人才子”所创作的昆腔传奇。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还说到“年来但儒之稍通音律者,伶人之稍习文墨者动辄编一传奇”,不仅名士才人好编剧,就是艺人也或参与其中了。这时期的传奇作者几乎达一百人,改编、创作的传奇近三百种,另有为数不少的无名氏作品。据吕天成《曲品》所录的“新传奇”,作者就有八十余人,作品总数已超过两百种。沈宠绥说“曲海词山”也不为过分。
这个时期出现了曲律大家沈璟和戏曲大师汤显祖,在进一步完善昆腔传奇格律和提高戏剧作品品位方面,各自作出了具有历史影响的杰出贡献。
沈璟,江苏吴江人,万历十六年(1588年)累官至光禄寺丞,十七年即辞官还乡,在家“日选优伶,令演戏曲”,钻研词曲声律。他也擅长唱曲,“每广坐命伎,即老优名倡俱皇迁失措”。作剧十七种,总名《属玉堂传奇》,写有散曲集和编选曲选。他在声律上的主要贡献是编有南曲谱《南九宫十三调曲谱》,还著有《正吴编》、《唱曲当知》,专谈昆腔字音的唱法。他创作了第一部传奇《红蕖记》后,对昆腔传奇提出了两大主张:“合律依腔”,“专尚本色”。这在他留存的[二郎神] 套曲中表达得非常充分。而后受他影响的作家很多,虽然有的作家并不完全赞同他的主张,但无形中形成了一个曲学流派“吴江派”,主要成员有吕天成、王骥德、卜世臣、叶宪祖、冯梦龙,还有顾大典、汪廷讷、史槃等人。
沈璟要求曲词完全服从曲律,甚至提出“宁律协而词不工,读之不成句,而讴之始叶,是为中之之巧(王骥德《曲律》引文如此说,而吕天成《曲品》引文谓“是曲中之工巧”)”,不恰当地对待词与律的关系,片面地强调了曲律。汤显祖是文学家,认为曲意是最重要的,不能以律害意。两人的争论是由沈修改汤的《牡丹亭》而引起的。沈的好友吕玉绳将沈改本给汤看,汤以为是吕改的,颇不以为然,在给友人凌檬初的信中微辞讥讽吕,说:“不佞《牡丹亭记》,大受吕玉绳改窜,云便吴歌,不佞哑然笑曰:‘昔有人嫌摩诘冬景芭蕉,割蕉加梅,冬则冬矣,然非王摩诘冬景也。”,在答吕玉绳的信中很明白地说出自己的主张:“凡文以意趣神色为主,四者到时,或有丽词俊音可用,尔时能一一顾九宫四声否?如必按字摸声,即有窒滞迸拽之苦,恐不能成句也。”汤的主张从文学上讲原本是正确的,但他在给友人孙俟居的信中却说:“自谓知曲意者,笔懒韵落,时时有之,正不妨拗折天下人嗓子。”这就同样走向片面性了。在当时,这种争论并没有发展下去,仅仅是汤沈之间的意见交锋,即在吴江派人的评论中也兼顾两者,最有代表性的是吕天成受王骥德的启发而提出的,如果能将两者结合起来,岂非是“双美”?这才是能让人接受的正确观点。
沈璟传奇十七种,“命意皆主风世”,数量虽多,但格调较低,仅有《红蕖记》、《埋剑记》、《双鱼记》、《义侠记》、《桃符记》、《坠钗记》、《博笑记》流传至今。《红蕖记》是部爱情戏,文词骈俪,自谓“字雕句镂,正供案头”,此后便倾向于本色。在场上演出较多的是取材于《水浒传》的《义侠记》,着重表现武松的仗义除奸和济弱助强,赞颂武松的“热心烈胆”,鞭笞世风败坏之情形意态。剧本曲白流畅,通俗易懂,也切合于人物个性,然缺乏韵味。该戏问世以后,“吴下竞演之”,流行了很久,其中《打虎》、《诱叔》、《别兄》、《挑帘》、《裁衣》、《杀嫂》,后来成为常演的折子戏。沈璟晚年所作的最后一剧《博笑记》,是部很有特色的作品。全剧以十则故事构成,长短随意,取可笑可怪之事,寓可叹可悲之意,用喜剧和闹剧的手法,反映了世态人情,大部分故事也有针砭时弊的积极意义。沈璟的作品在通俗化和适应演出方面主动做了探索,比如压缩传奇篇幅,《义侠记》三十六出,《博笑记》二十八出,净丑用苏人乡语,造语平实,尽量不用典故,这对普及昆曲艺术具有特殊的意义。
早在嘉靖中晚期和隆庆、万历初就从事昆腔传奇创作的作家有张伯起、郑若庸、屠隆、高濂等,而他们的主要活动时期是在万历年间。
张伯起,江苏苏州人,与梁辰鱼交往密切,喜欢吹箫度曲,也能粉墨登场。魏良辅改革昆山腔后,他就宗魏氏唱法。所作传奇七种,有五种传今。少年之作《红拂记》比梁辰鱼的《浣纱记》要早,是以唐人传奇《虬髯客传》和孟棨《本事诗》中徐德言与乐昌公主破镜重圆的故事捏合而成,以红拂与李靖的情爱为主线发展情节。此作虽不太成功,但使他获得盛名,“演习之者遍国中”。此后搁笔三十余年,于万历十四年(1586年)上太夫人八十寿而作《祝发记》,而后有《窃符记》、《灌园记》、《虎符记》、《扊扅记》、《平播记》等,后两种失传。《祝发记》也比较成功,而作者最得意之作是《扊扅记》,描写春秋时代的百里奚故事,可惜只存残出。
郑若庸,江苏昆山人,年辈比梁辰鱼略早,早年以诗名吴下。他曾编过类书,熟悉典故,他的《玉玦记》独好使事用典,成为明传奇填塞故事的滥觞,对后人产生不良影响。明王骥德、徐复祚等曲家对其批评甚烈。《玉玦记》写成的时间也在《浣纱记》之前,描写王商与秦庆娘悲欢离合的故事,剧中穿插了辛弃疾抗金的关目。其《赏花》出“游西湖”一套曲却极为流行。明吕天成评其曲“典雅工丽,可咏可歌,开后人骈绮之派”。万历年犹有《大节记》传奇,今不传。
屠隆,浙江鄞县人,精于音律,也能登场演戏。所作传奇三种,为《昙花记》、《修文记》、《彩毫记》,皆传。其中《昙花记》较为著名,常命其家僮演出,自鸣得意。此剧结构松散,关目繁冗,堆垛学问,多释道学理,立意不可取,然记中有几出只写宾白不填一曲,也是一种改革。《彩毫记》写李白事,词采较《昙花记》秀爽。
高濂,浙江钱塘人,所作传奇两种,以《玉簪记》最负盛名。《玉簪记》写潘必正与陈妙常的爱情故事,以刻画人物的心理活动见长,情景交融,富有诗情画意,又少用华丽的辞藻,雅俗共赏,很受观众欢迎。长年来盛演不衰,流传的出目很多,如《茶叙》、《问病》、《琴挑》、《偷诗》、《秋江》等至今还常见于舞台,《琴挑》中的[懒画眉]、[朝元歌]套曲传唱不绝。
以沈璟为领袖的吴江派作家较多,其影响一直延伸到明末,在此先说说万历年间的情况。主要的作家有卜世臣、叶宪祖、顾大典、汪廷讷、史槃等,另外如王骥德、吕天成、冯梦龙,王、吕、冯三人虽也编剧,冯又以改订他人剧本闻名,但三人均以理论研究影响为大。
卜世臣,浙江嘉兴人,所作《冬青记》、《乞摩记》传奇两种。仅存《冬青记》稍为可观,曾在苏州虎丘曲会上演出过。剧演宋陵被盗,唐珏收遗骨葬兰亭山下,植冬青树于上。后与林德阳会,同祭陵,见冬青枝叶繁茂,不胜感慨。吕天成评曰:此剧“音律精工,情景真切”,有“悲喷激烈”之情怀,所以在虎丘演出时甚为动人。
叶宪祖,浙江余姚人,多产作家,所作传奇、杂剧近三十种。其创作了许多短杂剧,大多为清赏消闲之案头剧,影响甚微。叶早年是沈璟的信奉者,音律甚严,当他中年创作《鸾媲记》时,借贾岛以发泄二十余年公车之苦,鸣个然文风倾向骈俪,宾白也用骄语,用典太多,到晚年作《长命缕》传奇,文风始有转变。
徐复祚,江苏常熟人,曲论家兼作家,创作态度很严肃,曾受沈璟影响。作剧甚多,所作以《红梨记》、《宵光剑》最为著名。《红梨记》演才子赵汝州与佳人谢素秋悲欢离合的故事,曲词秀美,用韵甚严。此剧系据元张寿卿《红梨花》杂剧改编,排场停匀调妥,佳思佳句,直逼元人。自问世以来,长期在戏场演出,流传的折子戏也多,有《访素》、《草地》、《窥醉》、《亭会》、《花婆》、《醉皂》、《三错》等,其《亭会》、《醉皂》为常演剧目。《宵光剑》写汉代名将卫青的故事,塑造了一个急公好义的铁勒奴英雄形象。后经艺人的不断加工丰富,成为净行“笑、叫、跳”看家戏之一。“笑”即铁勒奴,“叫”为《千金记》的项羽,“跳”是《西川图》的张飞。此剧《闹庄》、《救青》两出,是很有特色的传统折子戏。
王玉峰,江苏松江人,以《焚香记》著名。剧写人们熟知的王魁与桂英的故事,但跟南戏、杂剧有不同,替王魁做了翻案文章,将王魁与桂英的离散归罪于奸人,最后以团圆结局。该剧结构紧凑,曲词秀爽。明汤显祖评曰:“作者精神命脉,全在桂英冥诉几折,摹写得九死一生光景,宛转激烈。”即指该剧流传下来的折子戏《阳告》、《阴告》。
周朝俊,浙江鄞县人,以《红梅记》传奇著名。该剧以南宋太学生裴舜卿、郭稚恭等人跟奸臣贾似道的斗争为主线,穿插了裴舜卿与李慧娘、卢昭容二女的曲折的爱情故事。在折子戏的演出中突出了李慧娘的反抗形象,甚为感人,因此《鬼辩》一出流传至今。
许自昌,江苏吴县人,所作传奇以《水浒记》影响最大。该剧以表现宋江、张文远与阎婆惜之间的矛盾为主,穿插晁盖等人劫取生辰纲的情节,写至劫法场为止。虽然词尚骈俪,堆砌典故,极不切合剧中人物性格,但因故事通俗和表演精彩,在戏场流传至今。其《借茶》、《前诱》、《后诱》、《杀惜》、《活捉》等为常演的折子戏。
沈鲸,浙江平湖人,以《双珠记》、《鲛绡记》著名,均有传本。《双珠记》写王揖掣妻郭氏与子九龄投军,李克用欲夺其妻诬陷王楫下狱。郭氏决以死殉,卖子投渊,为神所救。后合家团圆。该剧情景奇苦,结构组织巧妙,穿插照应严密,其中卖子、投渊的情事令人惨然。但曲白未脱骈俪文风,风气使然。常演的折子戏有《卖子》、《投渊》。《鲛绡记》写宋代魏必简与沈琼英的曲折的婚姻事。当时苏州的申时行家班就以演《鲛绡》著名,人称“申《鲛绡》”。流传至今的折子戏有《写状》《草相》,尤以《写状》最为动人。
自嘉靖晚期至万历年间,北曲杂剧已趋于衰微,而南曲杂剧正在兴起,写南北曲短剧的作家也就多了起来,成了昆腔剧本的一种新的样式。嘉靖年间的梁辰鱼、汪道昆也写过短剧,主要的短剧作家有徐渭、王骥德、王衡等人。另有叶宪祖、吕天成、史槃、陈与郊等人,既作传奇,也作短剧。但南北曲短剧流行于戏场演出的仍属少数作品。
徐渭,浙江山阴人,诗、书、画、剧皆别树一帜,对后世的影响很大。明王骥德评其《四声猿》“故是天地间一种奇绝文字”。明汤显祖也曾叫奇:“《四声猿》乃词场飞将,辄为之唱演数通,安得生致文长,自拔其舌。”《四声猿》自嘉靖晚期问世以来,曲论家对其赞语不绝。《四声猿》为四种短剧的总称。《度柳翠》两折,北曲,写月明和尚度柳翠的故事。《雌木兰》两折,北曲,写花木兰女扮男装替父从军功成回乡的故事。《狂鼓史》一折,北曲,写袮衡击鼓骂曹的故事。《女状元》五折,有四折为南曲,写黄崇假女扮男装中状元的故事。明孟称舜称其为“创调”,系指在短剧中兼用南曲与北曲两种不同系统的曲牌。徐渭在嘉靖年昆腔新声产生之初,就在《女状元》中开创了南曲杂剧,并且在运用北曲套曲时也能变化灵活,曲词创作“有锋如电”,“奔逸不羁”,“不局于法”,难能可贵。所以说徐渭是昆腔初兴时期南曲短剧的先驱。其中《花木兰》、《狂鼓史》二剧最佳,昆曲至今能演《狂鼓史》,易名为《骂曹》。
王骥德,浙江会稽人,为徐渭门人。他的主要成就在于曲学的研究,后文再述。他写《男王后》杂剧,曲用北调,白不纯用北体,所谓“为南人设也”。当他创作《倩女离魂》杂剧时,一变剧体,四折全用“南调”,自此奠定了南剧的格局,“既遂有相继以南词作剧者”。可惜《倩女离魂》不传。据明末祁彪佳《剧品》说,自王骥德“与一二同志创之,今则已数十百种矣”。
南杂剧发展很快,这与昆腔新声的兴盛是很有关系的。但是,纯粹为南曲杂剧的还是不很普遍,南北兼体的不少,用北曲并未能打破元杂剧的体制,而仅注意于北曲杂剧的唱念的“南化”,后来大多成为“案头”之剧。
万历年间最著名的短剧作家还有王衡。
王衡,江苏太仓人,为大学士王锡爵之子,诗文甚佳,为人传诵。少年时曾和陶渊明《归去来兮辞》以劝父归隐,名动公卿。后来王锡爵家居时,魏良辅的传人张野塘等常去其家作客,王衡深受昆腔新声的影响。他所作短剧有五种,明沈德符《顾曲杂言》赞其“所作《真傀儡》、《没奈何》诸剧,大得金元本色,可称一时独步”。明祁彪佳《远山堂剧品》评其《真傀儡》曰:“境界妙,意致妙,词曲更妙。正恨元人不见此曲耳。”然祁氏说此剧为陈继儒作,存一说。该剧将官场比作戏场,写杜衍社日入市看傀儡戏,忽蒙圣上宣诏,杜未带朝衣,就穿上傀儡衣冠拜受救旨。情节构思,诙谐滑稽之极,寓意深刻。
汤显祖和他的“四梦”传奇
汤显祖是万历年最伟大的戏曲家,他的“四梦”传奇影响深远。“四梦”中的《牡丹亭》是最伟大的作品,流行歌场,家传户诵,几令元王实甫《西厢记》减价。
汤显祖(1550一1616年),字义仍,号海若,江西临川人。自署清远道人,所居名玉茗堂、清远楼。书香门第出身,十四岁进学,因拒绝首相张居正的延揽,二十一岁始中进士,任南京太常寺博士,后迁升礼部祭司主事。万历十九年(1591年)因上疏《论辅臣科臣疏》,弹劾首辅申时行,被谪为广东徐闻县典史。万历二十一年转浙江遂昌知县,为政清廉开明,接触了下层人民。万历二十六年告归家居,时年四十九岁。乡居十八年而卒。汤显祖少年时曾受学罗汝芳,罗汝芳为泰州学派王艮三传弟子,受统治者迫害始终不屈,与程朱理学有不同的观点,给汤显祖以很深的影响。汤显祖在南京任官时,又与东林党重要人物为友。在晚期又受批判程朱理学的达观与李贽的影响。因此,汤显祖的思想具有民主性和反理学的倾向。
汤显祖很欣赏徐渭杂剧的“奔逸不羁”、“不局于法”,也很欣赏《董解元西厢记》的“发乎情”如“铿金戛石”。他在《董解元西厢记题词》中说“志也者,情也”,认为写“情”必须包涵有思想意义。汤显祖早年即以诗文名,中年攻声律,晚年从事传奇创作,成就超过诗文,遂以传奇闻名。汤显祖藏书丰富,酷爱元人杂剧,有很深的作剧根底。明姚士粦《见只编》说:“先生妙于音律,酷嗜元人院本。自言箧中收藏,多世不常有,已至千种。有明朱权《太和正音》所不载者。比向其各本佳处,一一能口诵之。”汤显祖知律而不为律所拘,特别重视剧作的“曲意”,把“意趣神色”放在九宫四声之上,任凭才情进行创作。他与沈璟的曲学主张截然不同,曾有过一番争论。
汤显祖的传世名作为“临川四梦”,又称“玉茗堂四梦”,包括《紫钗记》(由早年习作《紫箫记》重写)、《牡丹亭还魂记》、《南柯梦记》、《邯郸梦记》。“四梦”的故事情节各有所出,除《牡丹亭》本自明人小说外,其他三种皆来源于唐人小说。汤显祖在剧中倾心于表现“情”的意义与生命力,渗透着大胆反抗封建礼教、肆意抨击官场黑暗的激烈情绪。这在《牡丹亭》里体现得最为充分。《牡丹亭》是明传奇中思想性和艺术性都达到最高成就的杰作。明王骥德赞曰:“其才情在浅深、浓淡、雅俗之间,为独得三昧。”明吕天成也说:“杜丽娘事甚奇,而蓄意发挥,怀春慕色之情,惊心动魄;且巧妙迭出,无境不新,真堪千古矣。”
《牡丹亭》主要写南宋南安府太守杜宝的千金小姐杜丽娘,为追求倾心的爱情和理想生活所经历的梦幻生死的奇异故事。该剧以杜丽娘的戏为主线,书生柳梦梅的戏为副线,并以封建性理和礼教的代表人物杜宝和塾师陈最良为对立面,展开“情至”与“性理”的斗争,塑造了一个既深受封建性理熏陶和封建礼教束缚、压抑的千金小姐,又是一个执著于“情至”、热烈追求自由生活的新女性形象。杜丽娘的形象包含着深刻的思想内容,散发着巨大的艺术魅力。汤显祖抓住“情至”这个主题,构思了为“情”生能死、死能生的梦幻般的情节,使现实生活与梦幻情境交错通变,戏剧矛盾极富有喜剧性,充满着浪漫的色彩。
杜丽娘是明传奇中最令人可爱的少女形象,她的出身和地位,决定了她要跨出反封建礼教这一步是很艰难的。她在学堂学的是《诗经》,受的是闺范教育,可她凭感觉却认为它是一首恋歌。在春香的怂恿下,她也会偷偷去花园游玩,可又说“步香闺怎便把全身现”,而内心却是“一生儿爱好是天然”。人的美好的心灵本不愿受压抑,受束缚。她到了花园,就深长地发出感叹:“不到园林,怎知春色如许?”接着唱道:“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朝飞暮卷,云霞翠轩。雨丝风片,烟波画船。锦屏人忒看的这韶光贱。”春色唤醒了她青春的活力,但只能把热烈的情感蕴藏在心中。杜丽娘游园后,“没乱里春情难遣”,竟得一梦,梦幻中不由自主地与书生柳梦梅去芍药栏前、湖山石边幽会。梦醒后,却还有心情想着那梦去不远。汤显祖奇妙地构想出让杜丽娘再去花园寻梦。这是幻中又幻的奇笔。杜丽娘边游、边思、边寻,这梦哪得能寻?一种长期受压抑的情感,就在梅树下迸发,唱道:“偶然间心似缱,梅树边。这般花花草草由人恋,生生死死随人愿,便酸酸楚楚无人怨。待打并香魂一片,阴雨梅天,守得个梅根相见。”沉重的哀怨正是对冷酷现实的控诉。
《牡丹亭》更感人的力量,在于它强烈追求个人的自由幸福、反对封建婚姻制度的浪漫主义的理想。这个理想,在汤显祖笔是以杜丽娘为“情”而死的代价,在不受封建性理束缚的鬼魂世界里去实现的。当杜丽娘不在现实世界里时,人的善良与美好的东西,都属于杜丽娘,她能按自己的本性去追求她的爱情,杜丽娘貌美,心美,行动更美,闪耀着动人的魅力,连冥间的鬼也被感动。当杜丽娘魂再一次得到柳梦梅的爱情时,不禁泪下,托书生开坟回阳,说道:“愿郎留心,勿使可惜。妾若不得复生,必痛恨君于九泉之下矣!”如此凄切之情,教铁石人也动心。柳生不负衷情,终使杜丽娘还魂复生。
正如汤显祖在《题词》中所说:“如丽娘者,乃可谓是有情人耳。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情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生而不可以死,死后不可复生者,皆非情之至也。”汤显祖描写的“情”对封建的“理”提出了有力的批判,表达了封建社会广大青年男女要求个性解放、爱情自由、婚姻自由的强烈呼声。这就是《牡丹亭》最伟大的成就。
《紫钗记》是由早年的《紫箫记》重写的。当年汤显祖因触犯张居正而落第之际,与同好“度新词与戏”,尝试着写作了《紫箫记》。此记还未完成就“是非蜂起”,因其作有所“讥托”,也非场上之曲,曲白骈俪,格调不高,汤显祖就放弃了。到了万历十五年(1587年)前后,汤显祖终于创作完成第一部技巧成熟的传奇《紫钗记》,对照前后“二记”,可以说是推倒重来的新创作。此记写霍小玉与李益的曲折爱情故事,以霍、李的“情至”,得助于黄衫客的“豪侠”,最后战胜卢太尉的强权,以“剑合钗圆”结局。明吕天成评曰:“描写闺妇怨夫之情,备极娇苦,直堪下泪,真绝技也。”
《南柯梦记》、《邯郸梦记》是汤显祖晚年于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至二十九年创作的两部传奇,习惯上称为“二梦”。“二梦”在结构上有相似之处,分梦前、梦中、梦后,而以梦境中的种种际遇为情节主体;梦前、梦后以实写虚,梦中以虚写实,突破了传奇生旦悲欢离合的旧格局。它们寄托着汤显祖的政治理想和对现实的某种否定,然而散发着浓郁的佛道思想色彩;在依然表现着“情”为主旨的创作思想同时,转而批判使人堕落的“矫情”;剧作的风格也有所转变,王骥德评曰:“其掇拾本色,参错丽语,境往神来,巧妙凑合,又视元人别一蹊径。”比较“二梦”,无论思想深度还是文辞风格,《甘卜郸梦记》更为优秀一些。
《南柯梦记》中的主角淳于棼原是豪杰之士,虽招为驸马,在太守任上甚有政绩,但是回朝拜相以后,笼络王亲贵戚,骄纵弄权,终于在宦场上堕落。这是汤显祖一直思索的问题,他用文艺的方式将它表现了出来,寄托着作者对黑暗政治的批判。而《邯郸梦记》中的主角卢生,却是个一生追求功名利禄、由书生而至权臣的更为典型的形象。卢生依靠有财有势的夫人,买通朝臣,中了状元,又以河功、边功为朝廷建立功勋。虽然有谗臣宇文融的算计和陷害,但宇文融被诛,卢生回朝做了二十年的宰相,“建功树名,出将入相,列鼎而食,选声而听”,可谓“得意”之极。尔后,五子俱蒙恩荫庇,皇帝钦赐园林、良马和仙音院女乐,卢生荒淫无度,最后一命呜呼。汤显祖以冷峻的笔锋,无情地暴露和批判了作为典型的封建官僚的一生,否定了封建社会的科举制和官吏制。这是其积极意义所在。而同时,“二梦”的佛道思想给作品带来消极的影响,也难以否认。但深入去研究汤显祖的思想和作品的艺术构思,那么,《南柯梦记》的“梦幻度世”,《邯郸梦记》的“八仙度卢”也可以说是汤显祖用以否定现实政治的一种方式。这是很重要的新认识。
“四梦”写成之后,就在歌场盛行。《紫箫记》初成,就由汤显祖至友玉云生“夜歌朝舞而去”,在广场演出,“观者万人”。《牡丹亭》的演出形成热潮,除汤显祖“自掐檀痕教小伶”外,太仓王锡爵“先令家乐演之,且曰:吾老年人近颇为此曲惆怅”。这是该剧演出的最早记录。后来出现了擅演杜丽娘的艺人,如罗章二、许钿、于采、王有信,汤显祖很为欣赏,他教罗章二“要依我原本”,赞许钿“慢舞凝歌向莫论”,赞于采“独身移向恨离情”,赞王有信“韵若笙箫气若丝”。至于有记载说杭州女伶商小伶演杜丽娘,“缠绵凄婉,泪痕盈目”,演至《寻梦》,随身倚地而气绝,那是明末崇祯时的事,影响很大。自《牡丹亭》问世,明代的邹迪光等很多家班演出不绝,成为昆曲常演剧目。“二梦”甫就,宜黄的伶人就学演,后来也流行歌场。汤显祖有《唱二梦》诗云:“半学侬歌小楚天,宜伶相伴酒中禅。”学界对于“四梦”演唱的腔调问题至今仍有讨论,胡忌认为宜黄的伶人当初是唱海盐腔的,万历三十年(1602年)左右,昆腔已经取代海盐腔的地位,宜伶学唱昆腔演“四梦”,那是很自然的事。所谓“侬歌”,就是指“吴歈”昆腔。这种说法很有道理。“四梦”流传至今的折子戏以《牡丹亭》最多,有十数出,常演的就有《学堂》、《游园》、《惊梦》、《寻梦》、《拾画》、《叫画》等,《紫钗记》有《折柳》、《阳关》,《南柯梦记》有《花报》、《瑶台》,《邯郸梦记》有《扫花》、《三醉》、《云阳》、《法场》。近年以来,全国各昆剧院团且卜演过各自不同的全本《牡丹亭》,影响远播世界各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