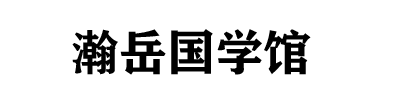昆曲历史:七、分化瓦解日趋衰败
太平天国时期的昆曲
太平天国时期的昆曲很少引起人们的关注,胡忌曾对此作过专门的研究,认为从时间和地域来说,太平天国的革命运动对昆曲发生过相当大的影响。太平天国革命从道光末咸丰初(1851年)金田村起义,在咸丰三年(1853年)就建立天京政权,同治三年(1864年)天京沦陷,最后在同治七年(1868年)被清军覆灭,前后坚持武装斗争达十八年。太平军与清军交战的主线从广西到湖南,转战湖北、江西、安徽、江苏、浙江等地,而后又有北伐西征,后期的重心又在江南一带,而这正是昆曲活动的中心区域。由此,不妨从随军昆曲和江南昆曲两方面来认识。
太平军多是广西人,对昆曲不甚熟悉,由于军事的需要,所以对三国戏和水浒戏很感兴趣,在军中和驻地常有这类戏的演出。太平军“皆尚戏剧”,而且在军中设置了随军戏班,直接为军事、政治服务,多半是徽班。据清李圭《思痛记》和王韬《瓮牖余谈》,其随军戏班“伶多皖人”,“于池州得戏班衣服器具数十箱,回金陵,乃招优伶装演,筑台于清凉山大树下,东王观之甚喜”。李洪春《京剧长谈》中曾谈到太平军的科班,如英王陈玉成在军中成立的“同春班”。同春班的少年艺伶,由著名艺人授戏,他们学戏、演戏,还要随军出征。他们的演戏除慰劳将士、鼓舞斗志外,还要向驻地民众宣传太平天国的革命,所演的戏就与一般戏班不一样,也跳“加官戏”,宣传的却是“上帝降福”、“天国万岁”、“忠勇永固”、“义气常存”等思想。
同春班重视生、净、丑,不重旦。在班中有著名的教师“江北三七”,即文武老生兼净老孟七、大武生任七和架子花脸张七,皆文武双全,又有擅演马超的夏奎章和擅演关羽昆乱不挡的王鸿寿。据说还有著名的昆丑杨鸣玉,也曾在同春班演戏。军中昆曲基本上是徽班中的昆曲,如关公戏,《斩熊虎》唱昆曲,《走范阳》唱二黄,《桃园结义》唱西皮,《封金挑袍》、《古城训弟》则唱吹腔。太平天国后期还编演过全本昆曲,如老孟七、周来奎、王鸿寿合作的连台本戏《洪杨传》,共四十本。他们随编随演,随演随编,以革命军的真人真事为素材,叙演创业的艰难。剧中人物不勾脸,不挂髯口,着装与生活同,全剧用昆曲唱,唱词通俗,武打精彩,纯是武术套数。该剧随着太平天国的失败而消亡,据说后来在江浙一带流行的《铁公鸡》,就是根据《洪杨传》歪曲改编的。
太平天国后期,在苏州忠王府曾有过一个戏班,能按昆曲传统演唱昆曲。据清谢绥之《燐血丛钞》,忠王李秀成之子静轩,欣赏苏州女优,“令忠府典采张老全教习梨园一部,选童男女一百二十人以习之,己亦学度昆曲。五月初五日,居然至忠府开台。静轩扮《絮阁》、《惊变》中唐玄宗,颇为忠王许可。中秋后,又选四十人习演武戏,合为一班。”忠王府戏班规模也不小。
苏州昆伶沈寿林、葛子香,也曾在太平军中演剧。太平天国革命失败以后,他们和孟七、任七也先后到过上海演出谋生。这时,苏州的昆曲“四大老班”也都转移到上海去演出了。太平军中也有随军到宁波而成为宁波昆曲主要艺伶的,如人称“苏州小花脸”的阿宁,参加了老庆丰班,小冬至到宁波后参加过瑞丰、老宝凤、老庆丰等班。在太平天国时期,苏州昆曲艺人的流散,实是苏州昆曲趋于衰落的原因之一。
北京的昆曲几起几落的昆弋班
咸丰以来,北京的面向演出市场的昆班已经绝迹,昆曲的演出只能搭入徽班,或入宫演出。如同治十二年(1873年)恭亲王奕诉喜昆曲,出资命昆旦杜步云成立全福昆腔科班,俗称“小学堂”。后来成为京剧先辈的钱金福、陈德霖等就是由该班启蒙的。一年后逢同治国丧停演,不久也就散了。同治年间,仍留在京的徽班的演出也不如乾隆末年,每场演出也不过带一二出昆曲。“雏伶昆剧,惟四喜最多,三庆次之”,四喜班有汪桂林、王桂官、赵桂云、薛桂芝等,三庆班有陈桂亭、乔蕙兰、沈芷秋等。而声誉卓著的艺人却是“昆乱兼擅”的名伶,如著名的“同光十三绝”,其中大多昆乱俱精,身怀绝技。如徐小香,是小生全才,擅昆小生戏极多;梅巧玲,是旦角全才;时小福,擅演昆正旦,人称“第一青衣”;朱莲芬,人称“第一昆旦”;余紫云、程长庚也是昆乱全才;尤其是杨鸣玉,即昆丑杨三,在北京极为著名,演昆丑“五毒戏”,无不精妙绝伦。光绪以后,南方昆曲艺人北上已经大为减少,留京的能昆曲的艺人不是改唱二黄,就是渐渐老死。据清《菊台集秀录》著录艺人八十二人,其中唱昆曲的仅十四人,兼擅的也只有六人。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以后的《新刊菊台集秀录》著录艺人一百零八人,昆乱兼擅的仅有七人,著名的有陈德霖、时小福、章铭坡。章铭坡,就是苏州大雅昆班后期的著名六旦“小金虎”,北上搭秦腔玉成班。据冯小隐《顾曲随笔》,庚子(1900年)以前,小金虎是玉成班的昆旦,其演“《刺虎》、《思凡》、《下山》、《荡湖船》,皆名著一时。每逢春令,各处堂会戏,未有不串金虎者”。庚子以后,小金虎离京南下,北京的昆曲大为逊色。
民国期间,北京的昆曲基本上附属于京剧班社,由于梅兰芳的积极提倡,学习、排练、演出昆曲,在京剧的舞台上始有昆曲的零星演出。梅兰芳从小学过昆曲,民国三年(1914年)以后,经齐如山建议,又陆续向陈德霖、李寿山、乔蕙兰学习昆曲,先后学会了数十出昆曲折子戏。齐如山《京剧之变迁》说:“到民国初年,梅兰芳又极力提倡昆曲,哄动一时。数年前演《思凡》、《琴挑》,总是满座。一天以《瑶台》演大轴子,梨园老辈群相惊异,说《瑶台》演大轴子,可算一二百年以来的创闻。”自民国四年(1915年)梅兰芳在那家花园演《思凡》起,五年内曾演了《金山寺》、《梳妆》、《游春》、《跪池》、《三怕》、《佳期》、《拷红》、《闹学》、《游园》、《惊梦》、《琴挑》、《问病》、《偷诗》等戏,演出效果极好,并带动了其他著名演员也演出了昆曲剧目,如红豆馆主、陈德霖、李寿峰的《奇双会》,杨小楼的《铁笼山》,程继先的《雅观楼》,钱金福的《山门》,程砚秋的《闹学》等。据朱家溍追忆,民国期间由京剧演员演出的昆曲剧目有近百出之多,包括老生、武生、旦、净、丑戏。另有富连成科班和中华戏曲学校也保留有一批昆曲教学剧目。
已经地方化的昆弋班自同治、光绪以来,几起几落,班社更迭,但培养了几辈演员,也可以说是惨淡经营了。
同治初年,在北京城内名公宗室私办有昆弋戏班。如同治二年(1863年)醇王府奕譞所办的王府“安庆班”,由“高腔刘家”主持,掌班人刘玉秀,演员多出身于道光年间的成王府小祥瑞科班的“祥字辈”演员,也有搭班的昆弋名伶。同治八年(1869年),该班招收旗籍、汉籍子弟十余人学艺,以“庆”字排行,有盛庆玉、胡庆元等,后成为昆弋骨干,世称“庆字辈”昆弋演员。安庆班前后历时十五年,于光绪三年(1877年)停办。光绪九年(1883年),醇王府复起“恩庆班”,领班人刘英,演员主要是原安庆班人,还将冀中白洋淀一带的昆弋艺人和乡镇戏班传入王府演唱。曾在王府演出和传艺的有向保刘、化起凤、郭达子、白永宽、张元红等。该班历时三年又停办,醇王将戏箱赏与生净全才白永宽,允其以“恩庆班”名义可在冀中各地演出。光绪十四年(1888年),醇王府第三次复组“恩荣班”,领班人为“高腔刘家”的刘福泰,演员有孝三丁、李仓儿、刘二福、盛庆玉、惠成、庆善、庆德等。该班招收了旗汉子弟三十余人,艺名排“荣”字。光绪十六年(1890年)底,醇王谢世,这个前后三期,陆续近三十年的王府昆弋戏班,终于报散,培养的“庆字辈”、“荣字辈”大批演员流入冀中、冀东乡镇,对昆弋派的壮大和发展起到一定的作用。
民间的昆弋班却基本上活动在河北农村,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如高阳县的“庆长班”、玉田县的“益合科班”、安新县的“子弟会”等。高阳庆长班年代既久,道咸年间就已成班,光绪年间成班次数亦多,多次起用化起凤为领班和主演,每次起班招集的基本上是白洋淀周围的昆弋演员。而本地人随著名演员学戏,已是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之后的事,如侯瑞春随朱玉铮习旦,侯益隆随邵老墨习丑兼净,韩子云随侯益太学花旦,马凤彩随陈之濩学花旦,侯玉山随邵老墨习丑兼净,齐凤山随徐廷璧习小生,韩世昌随韩子峰习旦,梁玉和随郭凤鸣习丑等。该班于民国五年(1916年)后始不组班。玉田益合科班,班主王绳。光绪十六年(1890年)开班,聘名师教习,招收本县及丰润县的学生三十八人,皆以“益”字排行,世称京东“益字辈”,如王益友、侯益才、侯益太等。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京东大饥荒,无力维持,遣散师徒自谋生路。后来又二起二落,至民国初年停办。安新县子弟会,属票会组织,由向保刘始办,活动时间较长,从同治中期至清末,培养了四期昆弋演员,如白玉柱、白永宽、化起凤、张元红、陶锅腔、朱玉铮、陶显庭等为光绪中期的演员,陶振江、白云亭、白月桥、白玉田、白云生、张德发等为后期的演员。北方农村昆弋班的发展始终受到北京王府昆弋班的支持和倡导,王府班散后,王府艺人会散落乡间昆弋班或子弟会传艺。而北方昆弋,最终又得依靠强盛起来的农村昆弋班重返城市。河北农村的昆弋势力对北方昆弋的发展起到相当重要的作用。
宣统二年(1910年),肃亲王出资,召集原王府艺人及流散的昆弋艺人,复组“安庆班”,管事为徐廷璧、张荣成、王益友、张荣秀四人。该班演出剧目甚多,人员为“庆”、“荣”两辈和冀东“益”字辈,以及冀中艺人大会师,在京中各戏园公演。然不到一年,辛亥革命爆发,该班解散,徐廷璧率一批演员再返河北乡间。宣统三年(1911年),高阳县有侯成章、侯瑞春等组成“荣庆社”,在当地演出。民国五年(1916年),新城县邓玉山、李宝珍组成“宝山合班”。同年,李益仲集合玉田、丰润两县的昆弋演员,以郝振基为主演,组成“同合班”。这些班社的组合相对比较稳定,为重返城市做了一定的准备。
民国六至七年(1917一1918年),是北方昆弋班很重要的两年。
自民国四年梅兰芳在北京演出昆曲以后,北京人对昆曲又产生了兴趣。民国六年宝山合班首次到冀东演出,大受欢迎。同合班转道三河,进入北京演于广兴园,郝振基以猴戏《安天会》等获得极大的好评。昆弋班在北京沉寂多年之后又有兴旺之兆。民国七年,高阳“荣庆社”进京,演于天乐茶园,实力雄厚的荣庆社演出大获成功,复聘邀郝振基等名伶入班,同合班即行瓦解。同合班演员回冀东加入宝山合班,当年夏季再次入京,演于丹桂园,仍不敌荣庆社。荣庆社又邀白玉田父子、侯玉山等加入荣庆社,宝山合班只得回乡。荣庆社集合了三个昆弋班的实力,在北京站稳阵地,昆弋班在北京一度兴盛。这时候的荣庆社韩世昌声名大振,在北京经昆曲名家赵子敬、吴梅等人的指点,又得前辈名伶陈德霖的教导,技艺精进,其表演“台步之工稳,喉音之嘹亮,神情之尽致,唱念之清脆”,在昆旦戏上开拓了新的领域,和同时的梅兰芳的昆曲并称。除韩世昌外,像武生王益友,净侯益隆、侯玉山,老生陶显庭、郝振基等,皆一时之隽选,当时工旦的白云生也是后起之秀。他们对北方昆曲支派的发展和延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民国八年(1819年),韩世昌、侯益隆、马凤彩等荣庆社部分艺人首次到上海演出成功。第二年初夏,郝振基、白玉田率荣庆社赴上海,郝以猴戏深获赞许,从而奠定了南北郑法祥、郝振基、杨小楼三大猴戏流派。民国九年(1920年)夏,河北束鹿县王芗斋、任瑜轩等组成昆弋“祥庆社”,邀去荣庆社的白玉田、王益友、侯玉山,而韩世昌又常与皮黄班合作,分散了荣庆社的力量。荣庆社不得不走上城市与乡镇的巡演道路。北京的昆弋班演出由此逐渐衰微。此时,昆弋祥庆社培养了新一代的“祥字辈”演员,如崔祥云、崔祥元、吴祥珍、吴祥生等,成为昆弋班晚期的骨干力量。但祥庆社像乡绅班一样偏安一隅,不进都市,五年后也就解体了。
20世纪20年代晚期之后,昆弋就逐步走向衰败,原来强盛的荣庆社也面临着危机。
民国十七年(1928年)秋,韩世昌等人曾赴日本演出四十天,是中国昆曲的第一次组团出国,获得日本文学界、艺术界的高度赞赏。韩世昌声誉日增,但昆弋的颓势终无力挽回。
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荣庆社终因班内矛盾激化,于深县散班。原荣庆社的白云生组织“庆生社”,在天津公演,因阵容齐整、剧目多样,在天津新欣舞台连续演出近半年时间。后因日寇入侵,时局动荡,演出入不敷出,忍痛解体。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冬,原荣庆社的侯永奎、马祥麟,邀集郝振基、陶显庭、侯益隆等,仍以荣庆社的名义在天津演出。而韩世昌和已改唱小生的白云生,邀集其他艺人搭入侯炳文所组的祥庆社,自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从北京出发,巡演东南六省,因“七七事变”,战事日紧,于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经天津回北京,不久散班。在天津的侯永奎、马祥麟等仍在支撑残局,后因洪水瘟疫,艺人有相继死去的,荣庆社终告结束。京津一带遂无昆弋班的声息了。
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日本投降,抗战胜利,韩世昌、白云生重组庆生社,演于北京建国东堂,也是昙花一现,不足半年,即告结束。北方昆弋完全息影,濒于绝迹。
苏州的昆曲及其向上海转移
苏州是昆曲的故乡,一向与北京处在南北并峙的局面。道光、咸丰以来,苏州的“四大老班”大章、大雅、鸿福、全福,在长期的演出实践中,已形成了各自不同的特点:鸿福班经常流转江湖,上海开埠后即进入上海;大章班、大雅班主要以上海为基地,并向上海京戏园输送了不少人才;全福班基本上在苏州演出,光绪年后也进入上海。这四大老班,因其年代久远,实力雄厚,故最为著名。各班均分坐城班和江湖班,江湖班活动在杭、嘉、湖和邻近地区,后期坐城班因观众减少也进行流动演出了。
咸丰十年(1860年),太平军攻克苏州,冲击了苏州昆曲,苏州的昆班从这时候开始几乎都转移到上海和杭、嘉、湖地区去谋生。著名的大章、大雅、鸿福也基本上在上海演出。从同治三年(1864年)起,所谓“省城克复”,昆曲艺人有先后回苏州的,同治七年(1868年),流散的部分艺人陆续回籍,并在老郎庙(梨园公所)开台试演。但此时苏州昆曲的经营演出,已经以上海为主要的基地,光绪年间苏州昆班的主要演员大多在上海演出。根据光绪七年(1881年)苏州《重修老郎庙捐资碑记》,当时“在申者尚存百十余名”,据陆萼庭搜访资料考证,在光绪三年至七年间,在上海演出的苏州艺人不仅包括四大老班的大部分成员,而且还有道光、咸丰以来的苏州昆班名伶。苏州艺人去上海演出,班名照旧,但艺人互相搭班,只求阵容齐整,门户观念早就淡薄。老辈艺伶有张八、王松,当时声名较大的有葛子香、邱阿增、周凤林、沈寿林、陆祥林、张茂松、吴庆寿、姜善珍、陆寿卿、金福、丁兰荪等。
留城坚持演出的昆班,力量相对就较弱,又遭遇乱弹班进入苏州,发生了“昆乱竞争”,使苏州昆曲维持为难。如光绪四年八月十一日《申报》载文《姑苏杂闻》说:“本城班脚色,拟欲搬至黄鹏坊桥汪姓宅中,所造房屋已由本地武班顶替,同时上场云。”所谓“本地武班”指苏州昆弋班。据光绪六年四月十一日《申报》载文《重整戏园》说:“苏省郡城陛庙旧有武班戏园一所,前因滋事封禁,歇闭多年。近日城内文班,知音极少,观剧者皆不喜昆曲而喜京腔。大抵阅者好武厌文,而演者不得不移商就徵,由是邀集武班脚色,拟就该处文武合演。现在戏园已经修理整齐,即日开台演戏云。”又据当月十七日该报《戏园押闭》报道:“前报苏垣郡城陛庙新开戏园,当时疑为文武合演之班,现悉开园者多系京班脚色。按苏城前因徽班在城曾酿盗案,株连昆班,经昆班申诉得雪,自此立案勒碑,不准外来各班入城演剧,事越数十年两碑石尚存。县署闻信,亦恐因此寻斗生衅,故特于月之初四日,伤差押令闭歇云。”这里所谓“文武合演”,是指昆乱合班,为时势所趋,后来戏园修好开班演出者多系京班。昆班受到了很大的压抑,于是旧事重提,翻出嘉庆三年(1798年)立碑事,再次由官方封闭戏园,禁止外地戏班入城。该戏班不得已在阊门外杨安浜另租房屋修成戏园,开台演出后,观众踊跃,形成城内文班戏冷落、城外京班戏热闹的场面。
光绪八年(1882年),情况略有好转,五月十七日《申报》《姑苏琐志》一文说:“苏省自弛禁演剧以来,计今共设有戏园三家。庙前之聚福昆班,亦相继开演,生意均称繁盛,而普安桥同乐园,行头脚色较为齐整,观者尤多……闻渡僧桥下塘及普安桥后,刻下大兴土木,不久即可落成,行将大张旗鼓,并闻设有女客观剧之所。”所谓“弛禁”,指光绪七年慈安太后病死禁演,至此时开禁。但戏园也仅三家,“生意繁盛”也只是一时的情况。第二年,上海的荣贵茶园迁来同乐园开演梆子,“吴人最喜新声,故连日座客极为热闹”,“来观者几无容足地”。“省城唯郡庙前一戏园,犹演唱昆曲,观者寥寥,远不逮城外京班之喧嚷”。这里,说到城内的聚福班,是陈聚林和陈福来发起组织的昆班,在此前城内的昆班有高天小班,在昆乱竞争的情况下,曾竭力维护所谓的“苏州风范”,但看到城外京班的盛况和受到上海昆曲竞演新戏、灯彩戏的影响,为了谋生,苏州的昆曲也有所变化了。同年八月二十五日《申报》新闻《戏楼坍塌》报道:“今年七月,城隆庙前开演文班,观者寥寥……班中欲别开生面,串成新戏一本,名曰《溯慈愿》。灯彩陆离,如《洛阳桥》之类,更有观音化身种种变幻,先期传布,于十七日开演,示巨是日观者云集,致将厢楼压塌。”尽管如此,也无法使昆曲的局面有所好转,在乱弹新声风靡苏州城的时期,光绪中叶苏州的昆曲已经基本上转向上海了。
苏州昆曲在上海的情况,下文再述。这里,需补说一下苏州四大老班的鸿福班外,还有一个人称“武鸿福”的昆班。它是同治年间创建于浙江绍兴的“鸿福昆弋武班”。光绪年间曾在苏州老郎庙挂牌,在苏州织造部堂登记、捐银,故允许其以“姑苏鸿福班”的名义在苏州一带演出,以演武戏为主,在观众中影响很大,与演文戏著称的四大老班之一的“姑苏全福班”并称为“文全福”、“武鸿福”。武鸿福领班是著名武老生汪宝有,演员三十余人,唱昆腔,也唱弋阳腔(实际为吹腔、咙咚调),常年流转在吴县、昆山、吴江等太湖地区和上海周边县镇,以及杭、嘉、湖一带,深受欢迎。
光绪末期,苏州的昆曲已经基本涣散,四大老班也已支撑不住,坐城班早已出外谋生,苏州昆曲几成广陵散。光绪三十年(1904年)大章、大雅解散,部分艺人归入鸿福与全福,留在上海的或转入京班,或为曲师当“拍先”。城内的聚福班也在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散班。光绪末,苏州地区的民众只知道还有“文全福”和“武鸿福”了。但这文武两班也每况愈下,曾经有过散班之举,后又改组或重组,在民国年间勉强维持演出。民国十二年(1923年)秋,文全福正式散班;民国十三年九月,江浙军阀爆发战争,“武鸿福”也随之正式报散。
上海的昆曲演出在“昆乱竞争”中趋于衰败
咸丰以后,上海成为近代昆曲活动的新基地,苏州的昆班转向上海后,曾持续演出到清末。昆曲在上海的演出历史,虽然也曾经有过一时的兴盛,但最终还是走向了衰败。上海三雅园的兴衰和昆旦周凤林的经历,就十分形象地反映了昆曲在上海的这一段历史。
三雅园兴建以前的昆曲活动,可以追溯到明代万历年间,那时的松江、青浦还属江苏省,而后的潘允端家乐已在上海城内豫园活动了。明末清初,上海仍有昆曲活动;康熙年间《长生殿》曾经在松江演出;乾隆、嘉庆年间,上海的昆曲已与苏州、扬州的昆曲有了联系,这种联系继续在发展。道光五年(1825年),吴门顾兰州在上海演出了女曲家吴藻的《乔影》。而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后,苏州的鸿福班和宝和班等则已经在上海竞演昆曲了。
近代昆曲在上海和三雅园可以说是荣衰共存的关系。三雅园创建于咸丰元年(1851年),是上海第一家专演昆曲的茶室戏园。即使在徽班南下、京腔盛演时期,它仍保持演昆曲的传统,前后坚持演出达三四十年之久。
早期的三雅园建在四牌楼附近的顾姓宅院,专演昆曲文戏,观众席不大,置五张方桌,一桌三人,俗称“五台山”。据赫马《上海旧话》,当时小刀会起义,进攻县署,还保护戏园,“国丧”(咸丰元年道光帝去世)期间照常开锣唱戏。清《海上竹枝词》亦云:“梨园新演《春灯谜》,城外人向城内跑。”昆曲的演出还很盛行。据清王韬《名优类志》及其《瀛壖杂志》,可知当时的昆班不仅有著名的大章、大雅、鸿福、集秀各班,还有宝和班的“新剧”,“亦高出一筹”。咸丰四年(1854年)正月,小刀会撤离时,戏园毁于战火。几年后,浙绍分所在小东门外另辟演出场所,沿用三雅园名义,照旧演出昆曲。
同治三年(1864年),昆曲艺人陆吉祥与人合资在石路花墙头重建三雅园,仍是吴歈雅曲之天地。苏州的大章、大雅、鸿福昆班依然在此演出昆曲文戏,名伶有葛子香、邱阿增、小桂香、王鹤鸣、陆祥林等,后来又有享誉沪上的周凤林加入,时所谓“三雅园文班唱昆曲”,在上海很有名气。但是,这时期昆曲在上海必须面对北来的徽班和京班,苏州昆班在上海的形势也发生了变化,形成“昆乱相争”的局面。徽班在同治初年就来到上海,在“满庭芳”戏园开台演出,一时盛行,人们争相趋之。后来京剧接踵而来,满台雏凤,誉满春江,徽班又不敌京班。当时在丹桂、一桂、天仙诸茶园的演出已由昆、徽、京并演转至徽、京并演。之后,京班以“丹桂园”为最,徽班也渐被削弱。与之相应,昆曲知音渐少,三雅园时开时歇,几度易主,到同治末,昆曲在上海已趋向于衰落。同治十二年(1873年)昊门隐生《前洋泾竹枝词》云:“共说京徽色艺优,昆山旧部倩谁收。一枝冷落宫墙柳,白尽梨园少年头。”
同治末、光绪初,三雅园为重整旗鼓在“昆乱竞争”中争取自己的位置,在宝善街重建戏园,其规模也向京班戏园靠近。当时三雅园的昆曲(大雅、全福、鸿福)也借其他戏园演出,参与竞争。如光绪三年(1877年)四月,大雅班借丰乐园演出,日夜两场,每场演二十出左右,纯是“苏州风范”,而报酬极为菲薄,远不及京班。后来,有不少昆曲演员,如邱阿增、姜善珍、小脚篮等,先后脱离昆班搭京班演出,有时应观众要求,也会演一台昆曲。如光绪五年(1879年)五月,在天仙园演出“全昆”,借以在京剧舞台延续昆曲的生命。但光绪八年(1882年)周凤林退出三雅园以后,三雅园昆班便难以维持了。
陆萼庭将三雅园的昆曲活动分作三阶段叙说,颇为详细。第一阶段至光绪四年止,昆班除保持乾嘉传统和苏州风范外,已经以新戏和小本戏参与“昆乱竞争”,如《描金凤》、《呆中福》、《南楼传》、《红菱艳》、《白牡丹》、《洛阳桥》等,新戏以灯彩为号召,《洛阳桥》最为著名,传统戏《思凡》也以灯彩戏路子演,名曰《大思凡》,又有玩笑戏《来唱》等,一时甚为热闹。第二阶段至光绪八年止,演出比较零落,昆曲艺人被分化,改隶京班的渐渐多了,周凤林崭露头角,不久也改隶京班,京、昆合演已成趋势。第三阶段至光绪十六年止,三雅园时辍时演,光景清淡,虽以大雅班新人如小桂林、小金虎为号召,也无济于事。延至光绪十六年(1890年),三雅园最终关闭,作为纯粹的昆班演出基本上退出了上海舞台。原来苏州昆曲一年之中来沪数次,逐渐减少为数年一二次,最后处于长期沉寂,在“昆乱竞争”中昆曲终于衰败。上海的昆曲演出进入到新的阶段,即以京、昆合演的形式延续其艺术生命。而后,在满庭芳、金桂轩等戏园演出中偶有打出“三雅园文班”的名义,但只是仅指其为昆曲文班少数艺人杂凑而已。
光绪十七年(1891年),三雅园关闭之后,作为京、昆合演的标志就是周凤林接管丹桂茶园。
周凤林,乳名小老虎,是光绪年间上海最著名的昆旦。据孙玉声《梨园旧事鳞爪录》,其最初在吴门小唱班习艺,后为三雅昆班台柱,同辈曾小视其非科班出身。然周凤林天性聪悟,为五旦,演《跳墙·着棋》、《佳期·拷红》诸戏,“风情旖旎,颦笑宜人,他伶无与抗手”。周兼擅刺杀旦,《盗令》、《游街》、《杀惜》、《刺虎》、《劈棺》等戏,“亦俱出人头地”。后来因昆曲“背时”,就兼习京戏,隶天仙茶园金台班,“自此声名雀起”。待其有了积蓄后就接管了丹桂茶园,京、昆兼串,被沪上誉为色艺俱佳之名伶。
周凤林是当时昆曲艺人与时变迁的一个突出的代表人物,但他仍以演昆曲为主,周凤林的昆曲艺术在京剧舞台仍然受到欢迎。周凤林主持丹桂茶园后,所演之戏常照顾与他同时的昆曲演员,如姜善珍、小脚篮父子之付、丑,小桂香、邱阿增之旦,周钊泉之小生,郝福芝之武生,演剧昆多于京,仍重文戏。其间,他还尝试过小本戏、灯彩戏、连台本戏,然而终不能挽救昆曲整体衰败的命运。光绪末年,周凤林退出上海舞台。
光绪年间,苏州昆班常不定期来上海作短期演出谋生外,宁波昆曲也曾经数次到上海演出,除文班外还有武班,然武戏不如京班受欢迎,也难以在沪驻足。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张园开始演出昆曲。张园是无锡富商张叔和的私家花园,名“味莼园”,于光绪十一年(1885年)始对外经营性开放。二十一年七月,苏州大章、大雅两班艺人以“味药园大洋房内三雅园文班”的名义演出昆曲。第一期为期两周,演出《冥勘》、《湖楼》等折子戏和小本戏《衣珠记》等,以及串折戏《连环记》、《琵琶记》、《钗钏记》等。然后去天福、丹桂等茶园演出日场,不久就回苏州了。自此以后,张园就成为继三雅园后的比较固定的昆曲戏园,昆曲艺人不定期作短期的演出。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文全福班也从苏州来张园演出,演员阵容虽然齐整,但光景依旧,也难以维持。该园的昆曲演出,断断续续,直到民国以后渐歇。那时昆曲文全福班艺人仅存二十余人了。
为延续昆曲生命创办昆曲传习所
民国初期,昆曲演出的处境十分凄凉。但社会上另一种形式的昆曲活动,却绵延不绝,那就是昆曲的“清工”与“清客串”。昆曲自产生以来,在明清两代,以清唱为主的“清工”代代相传,灯灯相续,在不同的时期参与昆曲的活动,著名的曲师,对昆曲的发展和提高曾有过的卓著的贡献。自乾隆年叶堂被尊为清曲正宗以来,叶派唱法代有传人,道咸年间传韩华卿,同治年间传俞粟庐。俞粟庐为近代叶派正宗的代表人物,在苏州、上海授曲多年,“俞派唱法”得以流传,其子俞振飞嫡传其宗。晚清时期,曲友拍曲的社集不少,直到清末民初,尚有多处,以苏州的道和曲社和上海的赓春社、平声社时间较久,影响最大。这时候的曲友,不仅清唱曲,而且还不时串演,在著名曲师指导下,“清客串”还相当流行。当时,著名的曲师有邱炳之、殷溎深、沈月泉、陈凤鸣等,与曲社的关系很密切。
而此时,作为职业昆班的“文全福”已馈不成军,老的已老,年轻的却不多,演出很少,日见败落。在民国年间最后有过两次演出:民国十年(1921年)七月,在上海城内劝业场原址“小世界”演出,阵容虽不弱,然十门脚色缺六门,老演员“不苍迈而自苍迈矣”。第二年十一月,在大世界共和楼演出,老生沈锡卿也参加了,最后是全班合演前本《呆中福》。演毕,文全福昆班至此正式宣告解散。
就在文全福班两次演出之间,民国十年八月,由昆曲家张紫东、贝晋眉、徐镜清发起,联合同仁集资组织的“昆曲传习所”在苏州成立,文全福部分老艺人被邀入所担任教师职,从事培养昆曲接班人的工作。昆曲进入了培养“种子”、延续生命的时期。
昆曲传习所选址苏州桃花坞西大营门五亩园,初由道和曲社社长汪鼎丞题名班牌“昆曲传习所”,拟聘张玉笙任所长。次年春,由实业家穆藕初接办,俞粟庐书题班牌“昆剧传习所”,孙咏雩任所长。全福班艺人沈月泉主教小生,沈斌泉主教付、丑、净,吴义生主教外、末、老生、老旦,许彩金主教旦行(后由尤彩云接任)。另有笛师高步云、拳术教师邢福海、文化教师周铸九。传习所曾两次招生,陆续招收了五十余人,学员大多为苏州艺人子弟及贫家子弟,年龄在九岁至十四岁不等。入所后试学半年,然后立“关书”,学三年,帮演二年,五年满师。教师教曲极为认真,学员以“拍曲”打基础,后学吹笛子和走步,半年至一年后始分行当,后亦有改行的,然后才开始学各行的戏,叫做“踏戏”。
据胡忌考,民国十二年(1923年)学员始取“传”字为艺名,名字的后一字以“金、玉、花、水”作边旁(花取草字头),“金”为净、老生、外、副末行;“玉”为小生行;“花”为旦行;“水”为付、丑行。时在学艺期间得“传”字者凡三十七人(后在实验演出期间略增几人)。在民国十三年至民国十五年(1924-1926年)帮演期间,这些学员已经在上海获得普遍的赞扬,尤其是民国十三年五月在上海笑舞台以“昆剧传习所”的名义第一次演出,学员演出折子戏四十八出,并有俞振飞、项馨吾、殷震贤等著名曲家加串名剧,嘉宾满座,盛况空前,是清末民初以来最为兴盛的一次昆曲演出。在此期间,上海粟社王慕诘为学员题书艺名。民国十四年十一月再次赴沪在笑舞台、徐园、新世界等处演出,其间增聘陆寿卿、施桂林为教师。当时,顾传阶、朱传茗、张传芳的生旦戏和施传镇的老生戏,已初露头角,斐然可观。经过两年的实验演出,于民国十五年学员满师,除上述四人外,优秀的学员还有周传瑛、顾传琳、王传淞、倪传钺、郑传鉴、包传铎、沈传银、邵传镛、汪传铃、沈传芷、姚传芗、刘传蘅、华传苹、姚传湄、华传浩、周传沧等。
学员出科后,由实业家严惠宇和江海关监督陶希泉投资将学员组成“新乐府”昆班,聘俞振飞为后台经理,委派林子彝、孙咏雩主持日常事务,租上海广西路笑舞台为专演剧场,于民国十六年(1927年)十二月十三日以“笑舞台新乐府昆戏院”名义开台演出。首场演出了《追信》、《拜将》、《佳期》、《拷红》、《借扇》、《挑帘》、《裁衣》、《梳妆》、《跪池》等戏,未及七时上座已满,为笑舞台开演以来未有之盛况。其间陆续向蒋砚香、丁兰荪、林树棠、林树森、王洪等京昆前辈学戏,还排演了一些小本戏,提高了表演技能,丰富了演出剧目。至民国十七年(1928年)四月五日合约期满,“新乐府”在笑舞台作了告别演出,时“传字辈”合影有四十余人。此后,又在青年会、新世界、大世界演出,也应堂会,“新乐府”赢得了苏州、上海观众的赞许。随着演员声誉日高,因待遇偏低以及内部的思想变化,又有台柱顾传阶弃艺就学而离班,“传字辈”师兄弟要求自立。民国二十年(1931年)六月,“新乐府”宣告解散。“传字辈”师兄弟回苏州自组“共和班”,在苏州演出。不久,重返上海,进大世界演出,易名“仙霓社”。
同年十月一日,“仙霓社”在大世界开台首演,一炮打响。此后辗转于上海、苏州和江浙一带城镇,备受观众欢迎。这是一个集体经营性质的昆班,社务由郑传鉴、倪传钺主持,沿着共和班的精神创业,“传字辈”演员三十余人,同舟共济。四五年后,“仙霓社”的演出生涯便陷入了艰难。但在表演艺术上由于不断的磨练和请益,却进入了成熟阶段。这时,施传镇的老生戏经沈锡卿的教导,能戏多且精;姚传芗的旦角戏得钱宝卿的真传,细腻妥贴;赵传珺改学冠生、小生,戏路很宽,无论唱做,都极出色。“传字辈”演员经昆剧传习所到新乐府,又到“仙霓社”,积累了乾嘉以来的大部分剧目,又在实践中不断串演新戏、武戏,打破昆曲不分武行的传统,形成了武生、武旦行当。“仙霓社”的演剧风格,既有严格的“苏州风范”,又能适应观众的需要发展传统的昆曲艺术,在昆曲的剧目和表演艺术上作出了种种努力,但为时势所迫,只能在困境中求生存,仍无力复兴昆曲的局面。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社务改由赵传珺、刘传蘅主持,不久又归郑传鉴负责,再度从上海出发,流动演出于杭、嘉、湖地区。历经半年余,返苏不久,施传镇罹病身亡,对“‘仙霓社”打击不小。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下半年起,“仙霓社”在上海福安公司游乐场演出,“八·一三”该处遭侵华日军轰炸,烧毁全部衣箱,被迫辍演,“仙霓社”名存实亡。翌年十月起,郑传鉴、沈传芷等十二人重新聚合,演出于上海东方书场、仙乐书场等处。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终因观众稀少,难于维持,遂于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二月在东方书场演出后宣告解散。
这时,留在上海的郑传鉴、朱传茗、张传芳、汪传铃、方传芸、华传浩,多半去当“拍先”(拍曲先生)。有的一度转向京剧,如王传淞、汪传铃、华传浩。郑传鉴后去上海戏剧学校任教,培养“正字辈”京剧演员。沈传芷、刘传蘅、赵传珺继续流转各地,不久,赵传珺贫病交迫,冻饿而死于上海街头。王传淞在短期和盖叫天搭班后参加国风苏滩社,后又引进周传瑛,开始了惨淡的昆曲零星演出。
朱国梁领班的国风苏滩社系“国风苏剧团”的前身,民国三十年(1941年)七月,国风苏滩社和振风苏剧社合并为“国风苏剧团”,演出于上海大世界。当王传淞、周传瑛加入后,情况就发生了变化,形成了一种奇特的演出方式:演折子戏时,常是两折苏滩、两折昆曲、一折滑稽戏;有时在同一折戏中,昆、苏混唱,因为苏滩能唱不少昆曲剧目。所以,该班可以称是“半副昆班”,当时仅有七个演员:王传淞、周传瑛,加上原来的朱国梁、龚祥甫、张艳云、张凤云、张凤霞(后易名张娴),还有一个“独角场面”张兰亭(要操弄多种乐器)。他们常年浪迹江湖,流转演出于苏、锡、澄、杭、嘉、湖一带的城镇、乡村,风风雨雨,备受煎熬。后来,另几个穷途无路的其他“传字辈”演员也被吸引到这个穷班,如周传铮、包传铎、沈传锟、刘传蘅。在“国风”的六位“传字辈”师兄弟,依附于苏剧,保留着昆曲遗脉一缕。值得一说的是,昆、苏合班使苏剧演员提高了演艺水平,而且具备了表演正宗昆曲的技能,上述张氏三姐妹成为近代昆曲男女合演的第一代演员,“国风”的子女随着戏班流浪学戏、拖拉上台,也就成为后来的“世字辈”的第一批接班人。
此外,在昆曲面临失传的严重时刻,各地的业余曲社的曲师、曲友,以及分散在各剧种的“昆乱兼擅”的演员,还有昆曲各支派的演员,为保存昆曲不使其绝灭而苟延余脉。